25年前,我和一個同學去造訪戈革先生,我們初次見面,相談甚歡。據這位同學後來告訴我,戈革先生事後對他說:「這個江曉原有些意思——他居然說自己喜歡香艷詩詞。」前輩高人判斷人物,常有見微知著之法,喜歡香艷詩詞的,本來大有人在,只是人們通常不好意思赤裸裸說出來,而本人卻不辭坦然自陳。
香艷詩詞,或稱為情色詩歌、色情詩,《中國性學百科全書》中使用的中、英文條目名稱是:艷情詩(erotic poems),各種名稱在各種讀者心目中喚起的對色情的想像或預期,程度各不同,本來也沒有什麼明確界限。古今中外,艷情詩都是源遠流長,套用一句古人陳言,那真可以說是「其來尚矣」——就是大有來頭的。
《詩》三百,思無邪
在中國傳統話語中,證明艷情詩「其來尚矣」的最佳途徑,當然是援引《詩經》——儒家經典,「六經」之一,其中《周南·關雎》這樣人所共知的篇什就不用說了,《鄭風》《衛風》《陳風》中還有更多香艷的篇章。
道學家朱熹在他評注《詩經》的著作《詩集傳》中,對《詩經》的大量篇章痛加貶斥,《國風》中被他直接指斥為「淫奔之辭」者至少有二十二篇,開列如下:
《邶風》:《靜女》
《鄘風》:《桑中》
《衛風》:《氓》
《王風》:《大車》《丘中有麻》
《陳風》:《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
《鄭風》:《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狡童》《褰裳》《東門之 》《風雨》《子衿》《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
》《風雨》《子衿》《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
《衛風·氓》和《鄭風·遵大路》本為棄婦之辭,朱熹也不肯放過,硬指為「淫婦為人所棄」。對於《鄭風》則尤為痛恨,他在《詩集傳》卷四中有一大段議論,堪為宋儒道學之論的典型標本: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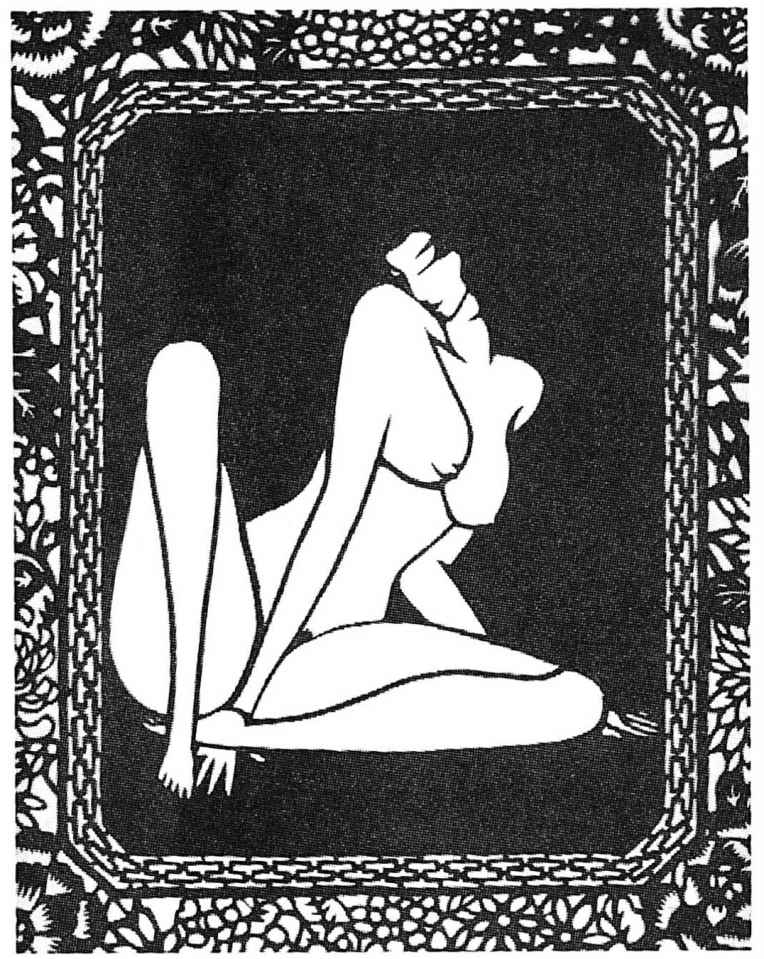
剪紙
這番道學言論之荒謬,只要指出一點就不難想見其餘——朱熹自己在《詩集傳》序中表示是相信「孔子刪《詩》」之說的,那麼《鄭風》中如此可惡的大量的「淫奔之辭」,「道大德全」的聖人孔子為何不將它們刪去,還要傳之後世貽害後人?何況孔子還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豈不是聖人也為淫張目?所以道學家們雖自命孔孟之徒,自許所言皆孔孟之道,其實離孔孟的原初學說甚遠。
其實《詩經》中,還有比上面朱熹所指斥的二十二篇更香艷的,比如《召南·野有死麇》,歌詠「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最後一章:「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女孩子那種既嬌嗔又情願,半推半就的情態,仔細體味起來,也真夠香艷的了。然而朱熹對這一章居然解讀成「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真是迂腐得可以。
朱熹因為是道學家,才對《詩經》中的艷情詩如此深惡痛絕,換到喜歡風流浪漫的文人那裡,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古代中國土大夫和官員們對色情文藝的欣賞和支持,今天來看頗有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者。明、清士大夫中熱衷於搜集、編輯和欣賞色情文藝的,大有人在。欣賞色情文藝給他們帶來快感。在一些序跋中,可以看到對這些快感的表達:
其間四時風景,閨怨情癡,讀之歷歷如在目前,不覺腹中多時積塊豁然冰釋矣。……雖未足動雅人之興,亦足以暢敘幽情。(《白雪遺音》高文德序)
批閱之餘,不禁胸襟暢美,而積憤夙愁,豁然頓減。……而其中之詞意纏綿,令人心遊目想,移晷忘倦,其亦可以步碧城十二闌干之後塵乎!(同書又序)
這還只是對民間情歌而發,讀後感中強調一個「暢」字。對於更多的色情或准色情作品,更有力的欣賞和辯護是強調「古已有之」:
仲尼刪《詩》,善惡並采,淫雅雜陳,所以示勸懲,備觀省。(屠隆《鴻苞·詩選》)
況乎釵飛釧舞,盡可銷愁;雨魄雲魂,原非著相。通青裙而下拜,纏紅錦以何嫌?……不知史氏非無別子,唐人亦有稗官。約指一雙,竟上繁欽之集;存詩三百,不刪鄭國之風。……但得指陳義理,悟入空空;何妨遊戲文章,言之娓娓哉?(鄒弢《青樓夢》序)
「孔子不刪《鄭》《衛》」是欣賞者和辯護者經常祭出的法寶,儘管這其間有那麼一點點偷換概念——《鄭風》《衛風》中的詩歌無論怎樣大膽謳歌情愛,畢竟沒有像明清色情文藝中那樣直接描寫性行為。如果《掛枝兒》《夾竹桃》中那些色情歌謠讓孔子見了,他是否會刪去,恐怕還在未定之天。
但大體而言,為艷情詩辯護,指出《詩經》中有《鄭》《衛》,與指出《聖經》中有《雅歌》,具有類似的效果。
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既有《詩經》這樣正大的源頭在前,艷情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然就源遠流長,生生不息了。
漢代艷情詩中就有一首來頭很大,即張衡的《同聲歌》,被南朝徐陵編的《玉台新詠》收在第一卷中。詩中有「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眾夫所稀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等句,以女性第一人稱的口吻描述了一個女子洞房花燭夜的經歷和感受。詩中所說掛在洞房牆上的圖,明代王士禎等人斷定那就是「秘戲圖也」,和張衡的另一篇作品《七辯》中「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夭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說的是同一回事。
上面引述鄒弢《青樓夢》序中提到的「約指一雙,竟上繁欽之集」,指的是繁欽的《定情詩》,也收在《玉台新詠》第一卷中,詩中有「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慇勤,約指一雙銀」等句。其實這首詩除了標題,內容也就是《周南·關雎》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的程度,遠遠談不上香艷,還比不上後來陶淵明的《閒情賦》呢——「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繁欽只是想像將飾品禮物一一放在女郎身上,陶淵明卻在想像中讓他自己對女郎身體的各個部位從頭到腳逐一親暱。
詩集《玉台新詠》,可以說是《詩經》以後直到唐代之前,這段時期內中國上流社會所創作的艷情詩的結集。南朝君臣在江左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他們大量創作屬於文人的艷情詩。比如梁簡文帝蕭綱《詠內人晝眠》:
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紋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恆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如劉緩《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工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當時很多文人以《三婦艷詩》為題賦詩,陳後主(叔寶)在這方面也不甘人後:
大婦年十五,中婦當春戶。
小婦正橫陳,含嬌情未吐。
這些詩篇,往往大膽而細膩地描繪美女的肉體,以及她們的美貌所喚起的文士們的性愛和感受,也不迴避輕浮的調侃——上面前兩首的結尾處都是如此。
南朝的艷情詩,在進入唐代時是完全「平滑過渡」的,只是看上去不像南朝君臣們那樣集中寫作——其實這種集中寫作的印象,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只是《玉台新詠》這樣的詩集給我們造成的印象。
談到唐代的艷情詩,不能不談到張文成的《遊仙窟》。
《遊仙窟》用第一人稱單數自敘旅途中在一處「神仙窟」中的艷遇。五嫂、十娘都是美麗而善解風情的女子,她們熱情招待「下官」,三人相互用詩歌酬答調情,那些詩歌都是提示、詠歎戀情和性愛的。因為性交、做愛之類的事畢竟不像別的事物那樣宜於直白說出,所以不免要發展出許多隱語,這些隱語又進一步發展成謎語,而且往往採用詩歌的形式,成為色情文藝中的一個特殊品種。先看《遊仙窟》中的例子:
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下官詠刀子)
數捺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十娘詠鞘)
誰都能看出來,這對男女借詠削水果的刀子,實際上是在說男女性器及其交合。後來在晚明的民間色情歌謠中,這種形式被大量使用。
隨著「下官」與十娘的調情漸入佳境,五嫂又不斷地從旁撮合煽惑,他「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忍心不得」,「腹裡癲狂,心中沸亂」,最後「夜久更深,情急意密」,終於與十娘共效雲雨之歡:
花容滿面,香風裂鼻。心去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插手紅褌,交腳翠被。兩唇對口,一臂支頭。拍搦奶房間,摩挲髀子上。一嚙一快意,一勒一傷心。鼻裡痠痺,心中結繚。少時眼華耳熱,脈脹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
這是中國文學作品中直接描寫男女性行為的最早段落,時間約在公元700年稍前。
在唐代文士筆下,性愛始終不是罪惡,而是他們樂意提到、樂意歌頌的意境。這可以從唐代詩歌中得到佐證。比如我們從李白詩中可以看到他對性愛的想像:
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寄遠》十二首之七)
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裡奈君何?(《對酒》)
到了元稹那裡,就能看到對性愛場景的直接描寫了,最著名的當數他的長篇五言排律《會真詩》,對仗工穩,辭藻華麗:
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發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
在韓偓的「香奩詩」中則有:
撲粉更添香體滑,解衣微見下裳紅。(《晝寢》)
但得鴛鴦枕臂眠,也任時光都一瞬。(《厭花落》)
眼波向我無端艷,心火因君特地燃。(《偶見背面是夕兼夢》)
李商隱一向詩意隱晦,但後人認為下面這些詩句都是暗喻性事的:
真防舞如意,佯蓋臥箜篌。(《擬意》)
想像鋪芳褥,依稀解醉羅。散時簾隔露,臥後幕生波。(《鏡檻》)
「橫陳」——躺在床榻之上的裸體美女,一直是文士們心馳神往的意象,是他們吟詠不厭的題目,除了前引南朝劉緩和陳後主的詩句,還可以看到更多:
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得橫陳於甲帳。(徐陵《玉台新詠序》)
嬌 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分,應憐秋夜長。(李百藥《雜曲歌辭·火鳳辭》)
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分,應憐秋夜長。(李百藥《雜曲歌辭·火鳳辭》)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李商隱《北齊》二首之一)
昔時知出眾,情寵占橫陳。(張希復《游長安諸寺聯句·道政坊寶應寺·小小寫真聯句》)
到了宋人筆下,也是繼響不絕:
愛隨青女橫陳,更憐素娥窈窕。(高觀國《東風第一枝》)
玉體橫陳,雲鬟斜墜,春睡還熟。(周邦彥《玉團兒》)
想得橫陳。全是巫山一段雲。(向子 《減字木蘭花·韓叔夏席上戲作》)
《減字木蘭花·韓叔夏席上戲作》)
再往後,文人們對艷情詩的興趣又有了新的發揮渠道,即在戲劇中加入一些色情段落。元代《西廂記》第四本第一折,寫到張生與鶯鶯幽會交歡,有人斥之為「濃鹽赤醬」。其實唱詞語句典雅華麗,最露骨處亦不過「我將這紐扣兒松,把縷帶兒解,蘭麝散幽齋。……我這裡軟玉溫香抱滿懷。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間花弄色,將柳腰款擺,花心輕拆,露滴牡丹開」等語,這只能算是「准色情」。在明清戲劇中,達到這種程度的段落並不少見。
明清戲劇中的色情或准色情段落,更多的是出自丑角的插科打諢,開一些與性有關的玩笑,例如:
自小生來貌天然,花面。宮娥隊裡我為先,掃殿。忽逢小監在階前,胡纏。伸手摸他褲兒邊,不見。(《長生殿·窺浴》)
更突出的例子見於《牡丹亭·道覡》一出。石道姑生為石女,婚姻失敗,不得已出家當道姑。她上場自述身世,全篇句句皆用《千字文》中的成句串成,卻句句皆不離開性和色情,而且還能押韻!姑舉其中描述新婚之夜的一段為例:
早是二更時分,新郎緊上來了。替俺說:俺兩口兒活像鳴鳳在竹,一時間就要白駒食場。則是被窩兒蓋此身發,燈影裡褪盡了這幾件乃服衣裳。天呵!瞧了他那驢騾犢特,教俺好一會悚懼恐惶。那新郎見我害怕,說道:新人你年紀不少了閏余成歲,俺也可不使狠和你慢慢的律呂調陽。俺聽了口不應,心兒裡笑著:新郎新郎,任你矯手頓足,你可也靡恃己長。三更四更了,他則待陽台上雲騰致雨,怎生巫峽內露結為霜!……新郎新郎,俺這件東西,則許你徘徊瞻眺,怎許你適口充腸?
這種文字遊戲,雖然純粹從文字技巧的角度來看頗見巧思,但終究格調不高,甚至顯得有些無聊。當時文人在戲劇中加入這類段落,主要是為了取悅和迎合觀眾與讀者——其中既有市井平民,也有官員文士。
民歌!民歌!
以前有一種非常流行的理論,認為「統治階級」的文士們在失去創作活力時,就會從民間文學中尋求靈感,汲取養料,所以他們會熱衷於收集和整理民間歌謠。而那些被收集整理的民間歌謠,即使是色情的,也因此而可以獲得某種合法地位——甚至在當今的文學史著作中也仍然有這樣的合法地位。可是如果一位今天的詩人,你也寫這樣的「黃色詩歌」試試看,你能得到什麼樣的地位?
這種詠歎讚美性愛的歌謠,早在南朝樂府詩中已啟其端。那些非常直露但仍不失其清新健康意境的短歌,是上層社會人士非常樂意欣賞的: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碧玉歌》)
開窗秋月光,滅燭解羅裳,含笑帷幌裡,舉體蘭蕙香。(《子夜四時歌》)
這些歌謠,常被稱為「吳歌」。
一提起「吳歌」之名,我們就應該想起李白的一些詩句: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烏棲曲》)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舞曲歌辭·白紵辭》)
使李白如此鍾情的吳歌,究竟是何寶貝?
吳歌者,江南歌謠,吳地之人所詠唱也。《晉書·樂志》說:「吳歌雜曲,並出江南。」吳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顧頡剛認為其起源「不會比《詩經》更遲」,其內容則主要是「小兒女口中的民間歌曲」。「小兒女」們口中最愛唱什麼?首先自然是男歡女愛、郎情姐意,此外當然也經常會旁及家鄉風景、人生苦樂之類。當年宋人編《樂府詩集》,就有「吳聲歌曲」,其中如《子夜歌》:
宿夕不梳頭,絲發被兩肩。
婉轉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這首歌謠的意境,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春圖中常有描繪——特別突出美人的長髮。而現今中外情色電影中,但凡拍到男歡女愛的場景,其中女性十九也是「絲發被兩肩」的。看來在這個意境上,東方西方,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又如《子夜四時歌》:
朝登涼台上,夕宿蘭池裡。
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蓮子。
「憐」者,愛也,又常以「蓮」字諧音代替,故「蓮子」者,即今日之「love you」也。(如今網上聊天之種種特殊用語,其實也有相似光景)當年使李白情有獨鍾之吳歌,即此類也。當然,和後來收集到的吳歌相比,上面這些歌謠可能已經經過文人的改寫潤色。
此後在敦煌曲子詞中也可以見到類似的色情民歌,姑舉歌詠美人胸部的數例:
雪散胸前。(《雲謠集·雜曲子·內家嬌》)
麗質紅顏越眾希,素胸蓮臉柳眉低。(《雲謠集·雜曲子·浣溪紗》)
青絲髻綰臉邊芳,淡紅衫子掩酥胸。(《雲謠集·雜曲子·柳青娘》)
胸上雪,從君咬。(《雲謠集·雜曲子·漁歌子》)
最後這句,有過甜蜜性愛的人都知道說的是什麼情景。從這些句子看,被文人潤色過的可能性不大,應該比南朝樂府中那些歌謠更本色些。
到晚明時期,對民間艷情詩歌的收集、編輯達到一個高潮。馮夢龍編輯了當時廣為流行的民間小曲集《掛枝兒》《山歌》《夾竹桃》等,風行一時。其中收集的都是南方吳語地區的民間艷情詩歌。這些民間小曲在歌詠、描寫男女性愛時比南朝民歌更為坦率直露。與這些民歌民謠小曲之類相比,文人的詩句恐怕還算不上真正的色情詩歌。文人的詩典雅華麗,看起來不那麼觸目,讀起來也不是那麼難以出口(本來就是文士們能夠吟誦的);而民間的色情詩歌或小調,那真是直白粗俗。下面先舉《夾竹桃》中兩則為例,這是晚明時期市民文學中色情歌謠的典型標本:
來時正是淺黃昏,吃郎君做到二更深。芙蓉脂肉,貼體伴君;翻來覆去,任郎了情。姐道情哥郎弄個急水裡撐篙真手段,小阿奴奴做個野渡無人舟自橫。(《野渡無人》)
瓜甜藕嫩是炎天,小姐情郎趁少年。紗廚鴛枕,雙雙併眠;顛駕倒鳳,千般萬般。小阿姐道我搭情郎一夜做子十七八樣風流陣,好像才了蠶桑又插田。(《才了蠶桑》)
這些用吳語創作的色情民歌,確實生動反映了晚明市民生活的一個側面。但是有些學者將它們說成「對愛情的熱烈追求」,或譽之為有「健康清新的格調」,甚至從中看出「反封建」之類的微言大義來,其實也大可不必。
有不少文人熱衷於搜集、記錄民間色情歌謠小曲,並在文字上做一些潤飾。在清代仍有步馮夢龍後塵收集改編民間情歌者,例如華廣生編的《白雪遺音》等。下面就是一首這樣的北方民歌,見《白雪遺音》卷二:
情人愛我的腳兒瘦,我愛情人典雅風流。初相交就把奴家溫存透。……象牙床上,羅帷懸掛鉤,哎喲咱二人,今夜晚上早成就。舌尖嘟著口,哎喲情人莫要丟,渾身上酥麻,顧不的害羞,哎喲是咱的不由人的身子往上湊。湊上前,奴的身子夠了心不夠。(《情人愛我》)
古代中國文人中普遍有著很深的「奔女情結」,這在民歌的搜集、編輯中也能反映出來。比如《白雪遺音》卷三中有一首《舟遇佳期》的敘事長歌,講一位「書生」坐船時,船家之女(當然是年輕貌美的)如何主動傳情、投懷送抱,與書生成就了雲雨之歡。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某些當代小說中的情節,例如在名噪一時的長篇小說《廢都》中,主人公莊之蝶和他身邊的那些美女們一場又一場男歡女愛的故事,就是中國舊文人「奔女情結」白日夢的生動寫照。
前面談到唐代《遊仙窟》中色情歌謠有「素謎葷猜」之法,在晚明民間色情歌謠中,這種形式被大量使用,所詠對像往往是生活中常用之物。舉兩例如下:
消息子(按:即掏耳朵的小勺),我的乖,你識人孔竅。捱身進,抽身出,踅上幾遭。捻一捻,眼朦朧,渾身都麻到。捻重了把眉頭皺,捻輕時癢又難熬。捻到那不癢不疼也,你好把涎唾兒收住了。(《掛技兒》卷八《消息子》)
結識私情像象棋,棋逢敵手費心機。……姐道郎呀,你攤出子將軍頭要捉我做個塞殺將,小阿奴奴也有個踏車形勢兩逼車。(《山歌》卷七《象棋》)
這些當然不是真正的「謎」,因為讀者一看就知道所詠的都是性交。如將《象棋》末兩句「謎底」直白說出,那就不成體統了。
這些歌詞要用吳語吟誦,方能傳神,經文人筆錄下來,如以普通話讀之,韻味要損失幾成,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就是20世紀學者所收集整理的吳歌,也依然只能如此——筆者數年前曾有小詩單詠此事:吳歌小史話當年,往事如煙已杳然,試唱吳聲白苧曲,風流千古在江南)。比如馮夢龍編的《山歌》中:
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來。
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連底湖膠打不開。
又如王翼之輯《吳歌乙集》中:
日落西山漸漸黃,畫眉籠掛拉(拉,吳語「在」也)北紗窗,畫眉籠裡無食難過夜,小奴奴房中無郎勿進房。
天上星多月勿明,河裡魚多水勿清,京裡兵多要反亂,姐妮房中郎多要亂心。
所謂吳歌,從南朝的《子夜歌》到晚明的《山歌》,鼎嘗一臠,豹窺一斑,大致光景也就不難推想了。
文人眼中的色情歌謠
古今文人,無不欣賞色情歌謠。他們除了抬出「孔子不刪《鄭》、《衛》」來為色情歌謠和艷情詩張目之外,還要從文學理論的高度來為色情歌謠辯護。
明清時代色情歌謠的辯護者們提出一個「真」字來與道學家的討伐相抗衡,表達這種思想最透徹的,可舉馮夢龍那篇短小而有名的《敘(山歌)》:
今之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於《掛枝兒》等。
馮夢龍在這裡強調一個「真」字來為民間的色情歌謠辯護。但是為什麼「真」能夠使得色情乃至淫穢變成可以接受的呢?近人王國維倒是有一段話,似乎恰恰是對此而發,其《人間詞話》中云: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語出《古詩十九首》之二)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 軻長苦辛。(《古詩十九首》之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乏病,而游詞之病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第六十二條)
軻長苦辛。(《古詩十九首》之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乏病,而游詞之病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第六十二條)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之句,若是與明清色情小說中類似情節的詳細描寫相比,恐怕也算不上「淫之尤」,然王國維畢竟不是道學家,他欣賞的所謂「真」,或近於「直率」。他又曾說:
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艷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據同上《人間詞話》刪稿第四十三條)
所謂「儇薄」者,無真情也,若出於真情,則雖「奸非」亦可恕,其他更可想見矣。「真」與禮教是難以相容的,《山歌》《夾竹桃》中那些直率表達著情慾煎熬和性愛渴望的女子,當然不是衛道士們希望的貞婦烈女。毫無疑問,她們和她們的情郎們,正是《繡榻野史》《浪史奇觀》中的男女。
收集和欣賞色情文藝,是文人的傳統愛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當然不是說每一個文人都如此)。如前所述,這件事能給他們帶來「暢」——也就是今天所謂的「快感」。就是高官大吏,理應為社會作表率的人,對於民間「私情譜」的歌謠集子,也會有興趣,例如鈕琇《觚剩》卷二「英雄舉動」條云: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掛枝兒》小曲與《葉子新斗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群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掛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蹐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
「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是否為反語?看來不是,因為熊廷弼為他排解了來自衛道士陣營的攻訐,這一行動客觀上至少是對《掛枝兒》之類作品的支持。
古代文人熱衷於搜集和把玩色情歌謠,現代文人學者同樣興趣盎然。馮夢龍編輯民間小曲集《掛枝兒》《山歌》《夾竹桃》的工作,受到當代鄭振鐸等民間文學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不要小看了這些「淫詞艷曲」,當年可是勞動了顧頡剛、劉復、魯迅、周作人這樣大名鼎鼎的學術界人物親自收集,甚至還勞動了蔡元培這樣的人物「登高一呼」,號召學者們從事收集工作!
魯迅早在1913年就主張收集民間歌謠,周作人則動手收集越中兒歌,但他們的努力沒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發揚光大」。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了校長蔡元培的啟事,號召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一起幫助收集民間歌謠;還刊登了劉復起草的《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不到半年,即徵集到1200餘首,並從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一首。
北大這番收集民間歌謠的舉動,頗使當時一些守舊人士痛心疾首。據顧頡剛回憶,許多守舊的教授和學生們歎息道:「北大是最高學府,《日刊》是莊嚴公報,哪能讓這種『不入流品』的東西來玷污它!」一位前清進士更是義憤填膺:
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領著一般年青人胡鬧起來了!放著先王的大經大法不講,竟把孩子們胡噴出來的……東西,在國立大學中,專門研究起來了!
然而,學者們卻對這種「胡鬧」樂此不疲。
顧頡剛1918年愛妻病逝,因悲哀過度而得神經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休養。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學日刊》,看見上面的歌謠,決定嘗試「把這種怡情適性的東西來伴我的寂寞」。他是蘇州人,就從自己孩子口中開始收集,漸至鄰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媽子……到後來,連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葉聖陶、郭紹虞等,都加入了幫助他收集吳歌的隊伍。顧頡剛收集的這些吳歌不久後在《晨報》——當時學術界都看這張報紙——上連載,使他在這方面又出了名,被目為歌謠研究的專家。後來出版的《吳歌甲集》就是顧頡剛收集的這些歌謠。當時竟有胡適、沈兼士、俞平伯、錢玄同、劉復五大名流,分別為《吳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吳歌的另一個干將是劉復(半農),江陰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陰船歌》比顧頡剛的《吳歌甲集》還早一年。且看一首:
新打大船出大蕩,大蕩河裡好風光。
船要風光雙只櫓,姐要風光結識兩個郎。
劉復還模擬民歌進行創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擬的江陰民歌。後來他又將目光擴大到俗曲——不附樂曲的謂之歌謠,附有樂曲的即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集,並進行研究,編有《中國俗曲總目稿》。
周作人當然也是歌謠收集研究中的大干將,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猥褻的歌謠》中,反覆強調收集民歌時不排斥猥褻的歌謠。這也可以說是歌謠研究者們的共同認識。起先在劉復起草的《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婦之辭,不涉淫褻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後發行《歌謠週刊》,新定章程第四條則說:
歌謠性質並無限制,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當一併錄寄,不必先由寄者加以甄擇。
於是周作人從《詩經》中的「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說到南唐李後主的「為奴出來難,教郎恣意憐」,再說到歐陽修的「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直說到《聖經》中的《雅歌》,以說明猥褻的成分「在文藝上極是常見,未必值得大驚小怪」,而對於猥褻的歌謠,「在研究者是一樣的珍重的,所以我們對於猥褻的歌謠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為難得似乎又特別歡迎」。真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也許最容易產生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這些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對吳歌之類的民間色情歌謠如此感興趣?
按照劉復的意見,如果要研究一個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個民族生活的真相,則民歌俗曲是「最真實最扼要的材料」:「因為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來陶情適性的;他們既不比考生們對著考官對策,又不比戲子們對著聽眾賣藝……民歌俗曲中把語言、風土、藝術三件事全都包括了。」胡適則著眼於文學:「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為方言文學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當然,這類意見只是就理論上言之,我想真正的原因,應該與古人編《樂府詩集》和《掛枝兒》《山歌》《夾竹桃》是一樣的,歸根結底還是文人的興趣。而文人們從來不缺乏為自己的興趣尋找正大理由的能力,找到的理由還總能與時俱進。
原載《萬象》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