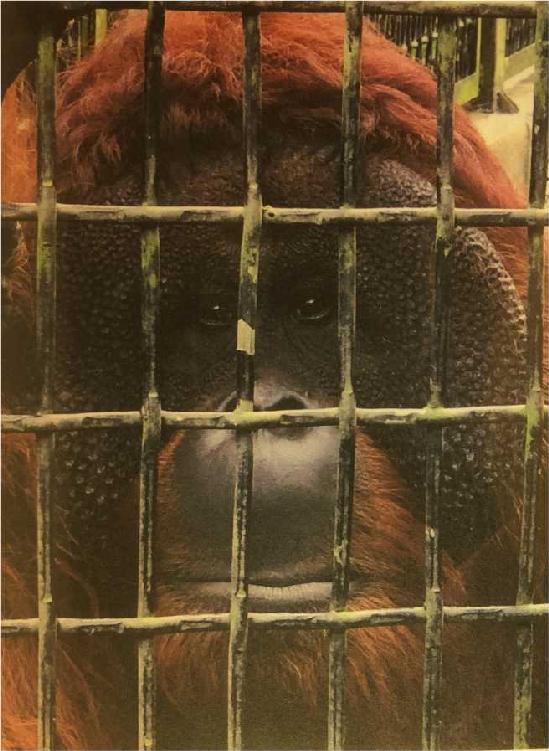我相信「初月帖」是他們之間的暗號,
在某一個月亮從丄頭升起的衣晚,當江水蕩漾著銀光,蘆葦中蛙聲四起,
那時那刻,他們還深信人間的愛和聚;可以天長地久。
有一天晚上到一個派出所去報案。所謂報案,就是報備遺失文件,立案了才能申請補發。
我可是在派出所裡頭長大的女兒啊,你記得嗎?五十年代的鄉村派出所或大一點的分駐所,位置一定在便於控管的要衝,基本上都是日本統治者精選的地點。軍艦灰的鐵製辦公桌,兩邊各有一落抽屜;桌面鋪著一塊大玻璃,從側面看,感覺玻璃是深綠色的。每一個警察的玻璃桌面壓著的,一定是家人照片。那時的人,多半沒有照相機,所以玻璃下大大小小的照片,不是笑臉燦爛的歡樂百態,而是照相館拍出來的正經八百的肖像。申請證照用的呆板大頭像之外,就是規規矩矩在攝影師一聲令下擺出姿態來的全家福,每個人的眼睛認真瞪著鏡頭,表情都像在說,不要眨眼,這輩子就這一刻,而且,照相好貴......
就這一刻
這種「這輩子就這一刻」式的黑白照片,總是讓我想起德國女朋友安琪拉說的故事:納粹對猶太人的壓迫越來越明顯的時候,鎮裡照相館的生意突然都發了。大家攜老扶幼地去拍「全家福」,她家的照相館一夜之間變成餐館一樣地川流不息。
「這輩子就這一刻」的時代情緒,在今天手機隨走隨拍隨刪的小確幸消耗時代裡,恐怕恍如隔世地難以傳達了。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有過「一刻」,很難忘。身為維也納頗有名氣的精神科醫生,他跟著維也納其他的猶太人被送進了集中營。有一次在轉送途中,他發現火車馬上要經過他的家,而所有的人都關在一節從外面上了鎖的悶罐車廂裡,只有一條破縫。幾個受難的同胞擠在那道縫前,死命盯著外面不斷掠過的光影。茨威格低聲下氣地請求這幾個人給他一寸空間,讓他看一眼他家破人亡的「家」,就那麼一眼、一刻、一瞬間,看一眼他此生再也無法見到的家。
如果是你,你會不會讓給他呢,美君?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在那個隨時有人窒息而死的悶罐車廂裡,每一個人都在縫裡尋找他破碎了的人和家。
轟隆轟隆火車瞬間就過去了,沒有人讓開。茨威格沒能看一眼那鐵軌旁的家,它永遠地沉入歷史的煙塵。
找人
我記得高雄茄萣鄉的一個警員,他也有兒子的照片壓在玻璃桌上,一個跟我同年剛考上初中的瘦小男生,兩隻耳朵尖尖往上豎著,像兔子。那一天消息傳來時,我正在廚房裡看你燒菜,菠菜丟下熱炒鍋嘩啦一聲,冒出熱氣,住在院子裡的另一位警員妻子衝進來淒厲地喊,「就是他們,就是他們。」
他們,警員父親帶著兒子共騎一輛摩托車去跟熟人借學費,一家一家去借,回家途中被火車撞上,連人帶車給拋進稻田里,當場死亡。也就是那麼一刻,家破了。
到今天,我仍然無法理解一個國家可以要求警察跟他的家人活在每日提心吊膽的風險中卻又給他低微的報酬和沒有尊嚴的生活。
「遺失什麼證件?」年輕的警員問。他的辦公桌,跟五十年代我熟悉的桌子差別不大。此刻他坐在桌前,我坐在桌側,彼此的方位如同他是問診的醫師,我是求助的病人。當他把資料一一鍵入電腦時,派出所入口的自動玻璃門突然打開了,一個矮矮胖胖的老婦人站在門,玻璃門因為她的體重暫時開著,她卻站在門檻不動,讓人擔心兩邊的自動門會馬上向她襲來。
她穿著拖鞋,七分長的花布褲,短袖花布衫,有點髒。頭髮燙得焦黃,一臉茫然,看著裡面忙碌的警察。有人招呼她進來,我乾脆起身走到門邊牽她的手,把她帶到我身旁的椅子坐下。
她惶惶然問我,「我女兒呢?」
「嗄……你女兒?」
我愕然看警察,警察邊打字邊說,「你坐一下,我們馬上幫你找喔。」
她很乖順地依傍著我坐著——現在任何人踏進來,會以為我們是一對報案母女了;我問她幾歲,她說八十五。問她名字,她說叫阿娥,問她住哪裡,她說派出所後面。她的手緊緊抓住我的手,眼睛始終充滿恐懼和惶惑,「女兒,我來找女兒,我女兒在哪裡?」另一個警察也從手邊的事抬起頭來越過兩張桌子對阿娥說,「等一下帶你回家,不要怕。」
警察把遺失證明遞過來給我,我問,「你們認得阿娥?」他點點頭。
「你們知道她女兒在哪裡?」他點點頭。
這倒蹊蹺了。到派出所來找自己的女兒,她女兒哪去了,警察竟然都知道?監獄嗎?送我到門口的警察小聲說,「阿娥女兒死了好幾年了。她天天來找,我們天天送她回家。」
初月
一張黑白照片突然從紙堆裡掉了下來,無聲地落在地板上,人像朝上,一個笑意俏皮的年輕女子對著鏡頭,雙眼皮非常鮮明。半高的領子立起,看得出是民國時代女學生的旗袍。
怎麼突然想起那張照片飄落的剎那?
小學校長余舅舅手裡拿著信,當著你,當著我們小輩的面,全身發抖,然後垮在籐椅裡抱頭痛哭。
凡是來自浙江淳安的你的男性同學或朋友,我們一概稱舅舅,不同於父親的湖南鄉親稱叔叔伯伯。在我們朦朧的認知裡,來自父親南嶽瀟湘的長輩,在戰場上踩過太多屍體,在離亂中見過太多悲慘,一般都有江湖風霜之剛氣。我們稱「舅舅」的,卻大多是文人氣很重的江南書生。余舅舅風姿灑脫,手裡常握一卷線裝書,寫得一手好字。他常常不打招呼,一推紗門就進來,用淳安話朗聲問,「美君小妹」在不在家。
這封信是寄給我,由我從美國帶進來轉給余舅舅的,所以我已先讀,而且怕轉寄遺失,鄭重地手抄一遍。余舅舅兩個月前寫了一封信託我從美國寄到浙江家鄉,今天得到的是第一次的回音。寫信的人有個素雅的名字:香凝。美君,在你似睡似醒的靈魂深處,是否還記得你的兒時玩伴香凝表姐?
「自君別後,」香凝的筆跡端整,每一筆一劃都均勻著力,「倏忽三十載……」三十年中,比當年戰爭和離亂更暴虐、更殘酷的國史在家鄉開展,香凝在人性崩潰的爛泥裡多次動念自殺,「念及君猶飄零遠方,天地寂寥,無所依靠,乃不忍獨死。」
分手時,香凝二十歲,寫信時已五十歲。「與君別時,紅顏嫣然,今歲執筆,凝已半百,疏發蒼蒼,形容枯稿。」但是三十年前在祠堂前分手那一刻的誓言,她我以為,接下來香凝要問的,當然是可憐的余舅舅是否也守了信約。我們知道他沒有。余舅媽就是同一個小學的國文老師,南投人。我們小輩去喝過他的喜酒,這表示他晚婚。
但是香凝的信,結束得太讓我意外了。交代完她自己的別後三十年,最後只有兩行字:「得去月書,雖遠為慰,過囑。卿佳不?」
美君,你不理解我的反應。我震撼得說不出話來,但是從來不曾跟你談過這件事。香凝最後的那句話,來自王羲之的「初月帖」:
初月十二日,山陰羲之報。
近欲遣此書,濟行無人,不辨遣信。
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書,雖遠為慰,過囑,卿佳不?
王羲之在一千六百年前寫給好友的信,說,「收到你上月十六日的來信,雖遙遠卻很欣慰,勞你萬端牽掛——你好嗎?」
香凝在生離死別、天地寂寥中苦等三十年之後,竟只輕輕問對方:卿佳不?我相信「初月帖」是他們之間的暗號。
在某一個月亮從山頭升起的夜晚,當江水蕩漾著銀光,蘆葦中蛙聲四起,那時那刻,他們還深信人間的愛和聚,可以天長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