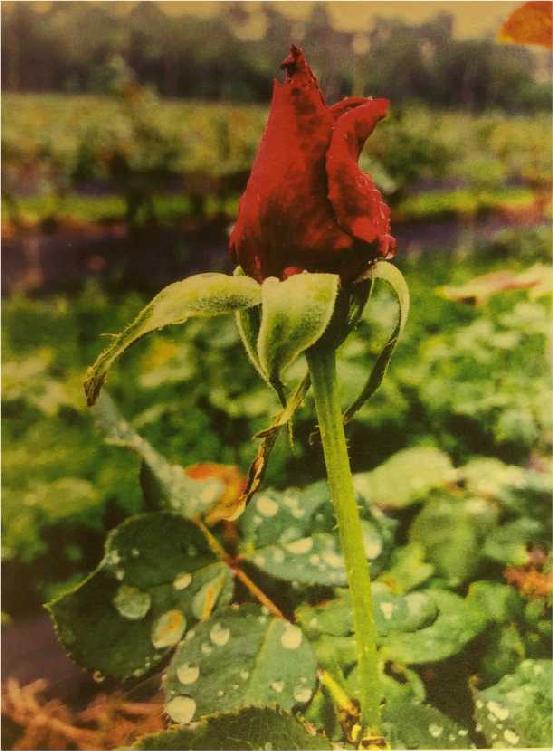臉上的皺紋都是她的,身上的關節都不是她的。
可是她眼睛裡的光芒、聲音裡的力量,
永遠是她自己的,獨一無二。
你記得安琪拉嗎?
八十五歲的安琪拉來信說她病了,我專程飛到德國去看她。人生歷練告訴我:超過八十歲的「閨蜜」生病了,必須排除萬難在第一時間探看。
從台北直飛法蘭克福十二個小時,從法蘭克福轉火車沿著萊茵河北走二小時,波昂站下車,再加十五分鐘計程車程,到了她家門口。遠遠就看見她的花園,她銀白髮亮的頭髮在一排紫丁香花叢的後面。聽見我的車門聲,她直起身,看向安靜的街道,然後笑吟吟地向我走過來,懷中是剛採下的大朵繡球花如孩子的粉臉,一派陽光燦爛。
我說,「原來你好好的,那我可以走了。」我作勢要掉頭,她抱著花大笑著走過來,我才發現,她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很慢。
我們就坐在那花園裡,在北國的藍銀色天空下,看著美滿得不真實的繡球花,有一搭沒一搭說了兩天兩夜的話。
風霜
人和人真的很神奇。有些人,才見一面就不想再見;有些人,不論你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成為朋友;有些人,即使在同一個屋簷下日日相見,也不見得在晚餐後還有話可說——晚餐嘛,還有食物的咀嚼和杯盤的叮噹聲響可以掩飾空白,晚餐後,那空白的安靜大聲到耳鼓發麻,你無可逃遁。
有些人,卻是從第一個照面,就知道,他是。
安琪拉大我二十歲。我們在紐約機場等候接駁車的空檔中聊了一下。那時的她才五十多歲,短短的卷髮,兩頰還有一點嬰兒肥的可愛感。二十年後第一次在銀幕上看見總理梅克爾,我失聲說,「這不就是安琪拉嗎?」
安琪拉堅持要為我泡茶、切蛋糕、洗葡萄。每一個動作,其實都很艱難。她拉開櫥櫃取出果醬,說,「此身一半不是我的了。膝關節、髖骨……」
「膝關節……那就不能騎單車了?」
她對我眨眨眼,笑了,「那也成過去了。」
安琪拉的兒子站在一旁,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我記得上一次站在這廚房裡,是安琪拉先生過世後五年,安琪拉六十五歲的時候。我說,「安琪拉,找個人去愛吧?」
她說,「男人多半笨。老年喪偶的尤其無聊,只會坐在家裡看電視,而且是看球賽,喝啤酒。」
安琪拉是一個愛看戲劇、愛讀小說、愛打抱不平、愛大自然、愛運動、愛社會正義、愛流浪狗、到老都天真熱情的女人,要怎樣去找到興趣廣泛、生趣盎然、不癱在沙發裡看球賽喝啤酒的進步老男生呢?
那次廚房會議的決議就是:到《時代週報》去刊登一個廣告。德國《時代週報》是一個知識菁英的報紙,以思想品味自詡。有整頁的交友廣告,廣告裡的女人多半宣稱熱愛莎士比亞,男人多半強調會背誦歌德。
安琪拉真的依照我們的廚房決議去登了一則廣告:
六十五歲女生,興趣:看戲、讀書、運動、大自然。
政治傾向:厭惡右,但絕非左。
外貌:腿力很好。
徵求興趣相近的男生從德國波昂騎單車到波蘭華沙。共九百七十六公里。
很多人來應徵,安琪拉最後挑了一個大概是「腿力最好」的男人,阿芒。兩個人清風明月、兩鬢風霜,騎單車共度了一個月。
花園外就是麥田,麥子熟了,整片田像一個方塊形的大盤,托著沉甸甸、滿盈盈的柔軟黃金,陽光刷亮了麥穗如花的芒刺。
我們在天竺葵旁邊坐下來。兒子已經識相地走開,讓我們女生單獨說話。
「阿芒呢?」我問。
安琪拉把枴杖小心地靠在門邊,拿了一條毛毯蓋在自己膝頭,說,「兩個月前走了。」
「走了?」
「突然的,三更半夜。他固定每週三來我這裡,那個週三他沒出現,半個月後我才知道。」
我想像事情的可能發生順序。阿芒是有家室的,他和安琪拉之間長達二十年的情份,是一個人世間的秘密。他的突然離世,沒有人會去通知安琪拉。所以,安琪拉經過的是什麼?等待,失望,不安,焦灼,直到發現阿芒爽約的原因時,非但無法執子之手溫柔告別,連告別式遠處的駐停凝眸都不可能……
全家福
我要安琪拉跟我細談她在波蘭度過的童年。
「你知道我是在波蘭洛茲長大的?」
「洛茲?」我從躺椅一下子坐了起來,「洛茲就是你的故鄉?」
十八世紀末強大的普魯士收編了部分波蘭國土,包含洛茲,緊接著鼓勵大批德國人到那裡定居。安琪拉家族幾代人就在洛茲生根。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軍隊入侵波蘭,洛茲變成一個關係特別緊張的地方——佔領者德國人聲色凌厲,波蘭人忐忑不可終日,猶太人沉默地等著大難臨頭,而像安琪拉這樣在波蘭已經好多代的德國人——「外省人」,尷尬地夾在中間。
「有一天大概清晨四五點鐘,突然很吵,」安琪拉說,「我爸硬把我從床上拖起來,讓我趴到窗口,不開燈。」
隔壁鄰居是猶太人。十歲的安琪拉目睹的是,荷槍的德國士兵闖入猶太人的屋子,驅趕還在熟睡中的一家老小,喝令他們立刻出去。安琪拉一家人眼睜睜看著隔壁鄰居家住在三樓的老奶奶,可能因為下樓的動作太慢,士兵把老奶奶直接從三樓窗口拋出來。
安琪拉在爸爸的懷裡,趴在窗口,全身發抖,爸爸在黑暗中說,「孩子,你聽好:我要你親眼看見我們德國人做的事,你一生一世不能忘記。」
被抄家出門、失魂落魄站在馬路上的猶太人到哪裡去了呢?
安琪拉說,洛茲有一個用高牆圍起來的區,看不見裡面,但是每次她經過,心裡都充滿恐懼。她模煳地知道,凡是進了這裡的人,都不會活著出來。全城的猶太人,都進去了。
安琪拉的家是個照相館,爸爸是攝影師。德軍進駐洛茲之後,照相館的生意突然爆紅。村子裡的人每天在門口排著長龍,等候拍全家福。
「因為,」安琪拉說,「本地人覺得時局不好,很不安;猶太人當然更覺得是世界末日,恐怕馬上要生離死別,而村子裡的德語人則擔憂自己的兒子恐怕很快會被德軍徵召當兵,所以大家都趕著來拍全家福……」
有一天,外面排隊的長龍裡似乎起了爭執,突然人聲嘈雜,安琪拉的父親停止拍照,出門去看。原來是隊伍裡的幾個本地德語人認為波蘭人現在沒有資格排到前面,要他們排到隊伍後面去。安琪拉看見照相師爸爸對著這些講德語的同胞非常憤怒、非常大聲地揮手說:
如果要在我這裡拍照,就請排隊。如果不願意排隊,可以,就請你們到別家去,我這裡恕不奉陪。
大家就安靜了下來。
好樣的
傍晚,安琪拉拄著枴杖和我走到村子盡頭一片草原上採集野生的洋甘菊,她是個大自然的信徒。早餐,配的就是採回來的洋甘菊。喝茶的時候,我八十五歲的閨蜜說:「應台,戰後很多德國人說他們當時不知道有集中營這回事。我想說的是,如果十歲的我就知道洛茲有個殺人的地方,你大人敢說不知道?也不要跟我說,國家機器太大、個人太小,個人無能為力。我父親就用他最個人、最微小的方式告訴十歲的我說,個人,可以不同。個人,就是有責任的!」
我看著她。八十五歲的安琪拉,臉上的皺紋都是她的,身上的關節都不是她的。可是她眼睛裡的光芒、聲音裡的力量,永遠是她自己的,獨一無二。
在安琪拉的身上,我也看見你,美君。日前在整理舊物時,翻到你回憶錄的這一頁,說的應該是一九四三年,你十八歲:
兵荒馬亂,大家都怕兵。一個憲兵隊駐在淳安城裡。有一天,我家隔壁不知道鬧什麼事,幾乎要打架,很多鄰居看熱鬧。這時憲兵來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當事人和一二十個一旁看的人全都抓走了,關起來,一關就是三天,而且不許家屬探訪。小老百姓不懂法律,害怕家人是不是會被憲兵槍斃,嚇得半死,來找我,我才十八歲。他們說,大小姐,這街坊只有你會講國語,求求你去憲兵隊溝通吧。
我也很怕,但是怎麼辦呢?
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我一個人走到了憲兵隊,抱了一大包熱燒餅。
見我的是位中尉排長。我說,我是來看我的鄰居們的。他說,上面不准見。我說,他們犯了什麼罪,這麼嚴重。我受鄰居之托,要求不大,只想看到他們是死是活。
他考慮了很久,最後說,好,可是你帶來的東西不能帶進去。我說,好,不給他們吃,只是給他們看,表示我的人情到。
排長勉強點頭。
我走到犯人間,他們一看見我就同聲哭叫:大小姐救救我們,我們已經三天沒吃飯了,快餓死了。
我毫不考慮,當下就把燒餅用力丟進鐵窗裡,鄉親搶著吃光了。
守門的憲兵報告排長說我不守信用。我很生氣,對排長說,「這世界上哪裡有餓罪?就是犯了死罪,也要給犯人吃飽才槍斃。我是可以告你們達法的。」
排長看看我,不回話。
第二天上午,所有的犯人都放回家了。
十八歲的女生美君,好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