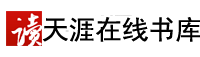縣上這次要劇團下鄉巡演,其實,是為瞭配合商品觀念教育活動。
易青娥要不是當瞭縣政協常委,咋也弄不懂,商品觀念教育活動是個啥。開瞭幾天會,腦子裡整個灌的都是這幾個字。聽其他委員說,寧州是緊挨著關中平原的一個小縣,隻沾瞭八百裡秦川的一點邊邊。而絕大部分都在秦嶺山區,相對封閉落後。人是自耕、自種、自吃。所有東西,都不知拿出去交換,所以日子越過越窮。據說寧州過去也有茶道、鹽道的。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經過這個縣的一條古道。順著這條古道邊上,過去有集市。後來通瞭汽車,古道才慢慢廢瞭。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資本主義尾巴”,“割”得連尾巴骨都不見瞭。這次全縣商品觀念教育活動,用一個領導的話說,就是要讓這些集市重新活起來,讓大傢都要學會做生意。劇團演戲,就是為瞭把人都召集攏,然後好開會。開會先是領導講話,然後是會做生意的人現身說法,再然後才演戲。
第一場演出,易青娥把大頭包瞭兩次,戲還是開不瞭。開戲前,她舅胡三元先是領著武樂場面的幾個人,敲瞭半天銅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圍到舞臺前邊來。據說,鄉政府提前用喇叭喊瞭好幾天,說劇團要來演戲,演楊傢將,還是大本戲呢。要大傢來看戲時,把傢裡能拿出來賣的東西都拿來。可喊歸喊,來的人大多還是空腳吊手的。有人手上拿瞭自編的竹籠、笊籬、草鞋、鍋刷子,還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擺,一直吊拉在身後。更沒人敢吆喝瞭。大傢都朝土臺子上死盯著,看劇團人敲鼓打鑼。有人議論說:“人傢劇團,那才叫敲鼓打鑼呢,聽那聲響,都是有下數的。”還有人說:“你看那敲鼓的,半邊臉雖然黑些,可手上、嘴上、臉上,還有溝子上,勁可都是渾的。哪像咱們這兒‘打鬧臺’,都是半夜聽著雞籠門響——胡(狐)敲哩。”
還有好多人都鉆在後臺,看演員化妝。鄉上安排維護秩序的人,攆都攆不走。前邊會議開始瞭,有人喊叫,都到前邊去聽會,就是沒人去。最後,是幾個人拿瞭長竹竿,見那不走的,就朝身上、頭上亂磕,才慢慢把人趕到臺前去瞭。
易青娥包的大頭正難受呢,隻聽有人喊:“快看,快看臺上。”
易青娥就從後臺朝前臺看瞭一眼。隻見舞臺上,樹林一樣,吊出一臺黑臘肉來。這些東西,她都認得,過去自己傢裡也有過。可最多也就是幾十塊。鄉下人過年殺頭豬,是要管一年的。沒辦法存放,就隻能吊在灶頭上,任由煙熏火燎著。這樣也可以保存很長時間不壞。有那日子過得好些的人傢,還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這些吊在舞臺上的臘肉,明顯有很多都是陳年貨,已經被煙火熏成黑炭狀瞭。隻見主持人把話筒嗵嗵嗵一敲,喊叫說:“都不說話瞭。現在,開始開會。銅場鄉商品觀念教育活動現場會,現在開始。首先請閻鄉長講話。大傢拍手歡迎!”
隻見那個叫閻鄉長的走上臺,第一句話就是:“大傢認得這是啥?”
底下喊叫:“臘肉。”
易青娥看瞭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觀眾。
閻鄉長又問:“臘肉是幹啥的?”
底下回答:“吃的。”
回答完,全場又哄笑起來。
隻見閻鄉長搖搖頭說:“不是吃的。這個臘肉可不是吃的。它是給灶司老爺吃的。給煙火吃的。給蟲吃的。不是給人吃的。大傢能猜猜這是多少塊臘肉?”
底下有人亂喊一百塊的,有喊一百五的。也有喊二百塊的。還有喊二百五的。
隻見閻鄉長把頭又搖瞭搖說:“都沒猜準。這臺上一共擺瞭三百一十七塊臘肉。你們能猜猜,是從哪兒弄來的?”
有人喊叫:“鄉上沒收下的。”
有人喊:“割尾巴割的。”
閻鄉長急忙糾正說:“可不敢亂說噢。鄉上這幾年可沒亂割誰的尾巴,也沒亂沒收誰的東西瞭。這是我們借來的。能知道是借誰的嗎?”
有人亂喊道:“地主老財的。”
還有喊叫黃世仁的。
又惹來一片笑聲。
閻鄉長就說:“這既不是地主老財的,也不是黃世仁的。這是離咱們鄉政府,有十五裡地的姚傢灣村,姚長貴傢裡的臘肉。”
“啊!”大傢一片議論聲:姚傢有這麼多臘肉啊!
閻鄉長說:“想不到吧。大傢再猜猜,這臘肉最長有多少年的?”
底下又是一片亂猜聲:三年,五年,八年,也有喊十年的。
閻鄉長又搖搖頭說:“你們還沒猜對。這三百多塊臘肉中,還有十四年的陳貨。已經讓蟲吃得隻剩下骨頭架架瞭,但人還沒舍得吃,也沒舍得扔。就那樣一直吊著。”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聲。
後臺也引起一陣議論聲。
閻鄉長繼續說:“他們是肉多吃不完嗎?不是的。是舍不得。姚長貴傢六口人,平均兩年殺一頭豬。一頭豬,能砍出五十幾塊肉來。你們能看見,肉塊都砍得不大。加上豬頭、豬蹄子,還有豬溝子、豬項圈,反正超不過六十吊。兩年六十吊。十四年加起來,也就是四百二十多吊肉。這臺上是三百一十七吊。他們大概吃掉瞭一百一十多吊。平均一月吃不下一吊肉……”
底下還有人喊叫:“那是好日子呀!”
閻鄉長說:“是的,是好日子。可要是把這些肉,不這樣朝壞地放,讓它們像商品一樣,流通起來,會是更好的日子……”
在臺下一片議論聲中,閻鄉長又給大傢算瞭算,那沒有吃的三百一十七塊臘肉的商品價值。易青娥的頭,就被水紗勒得陣陣幹嘔起來。好多演員都喊叫堅持不住瞭。有人就問朱團長,會到底還得多久。朱團長問鄉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鄉長會講多長時間。這陣兒,賬正算得細發。連底下觀眾都跟著算瞭起來。朱團長就說,讓大傢把頭先抹瞭,等會快完瞭再包。
會整整開瞭一個多小時,要不是閻鄉長會講,觀眾早都鬧騰起來瞭。他們在第二個點演出時,觀眾就把村上領導的場子給砸瞭。
那是一個很偏僻的村子。聽說劇團演戲不要錢,村上一個年輕人,就煽惑商品觀念教育活動帶隊的,還有朱團長,說無論如何,都要去他們那兒演一場《楊排風》。他說,戲太好瞭。他們村子自古以來,就沒正經唱過戲。要是縣劇團能去他們那兒唱一回戲,讓他給劇團一人磕個頭都行。朱團長問他是幹啥的,他說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傢想著,那不是支書就是村委會主任瞭。朱團長問有多遠,他說翻過一個梁就到瞭。小夥子怕領導們不同意,還專門湊到易青娥跟前,說她是主演,在團裡說話一定很響,要她幫幫忙。易青娥知道鄉下人想看戲的心情,但又不敢給領導建議。最後,是朱團長問她,到下一個演出點中間,加一場戲,吃得消不?易青娥急忙點瞭點頭。朱團長就同意去瞭。小夥子連夜發動村上人,大大小小來瞭三十多個,最小的,還有十一二歲的娃娃,把戲箱肩扛背馱著回去瞭。
第二天一早,劇團人就朝梁上走。村上來瞭兩個領路的娃,一問,一個十一歲,一個才九歲。易青娥覺得特別親切,就一直緊跟著。翻過一座梁,她問還有多遠,他們說快瞭。翻過一座梁,又問有多遠,他們還是說快瞭。六十幾號人,從早上九點出發,直爬到過瞭中午十二點,問娃,還是說快瞭。可朝前看,除瞭山梁,還是山梁,連一點煙火氣都尋不見。大傢又渴又餓,就發起瞭牢騷。也有那好開玩笑的,還把兩個領路的娃,押到路邊審問起來:“八格牙路,再哄人,死啦死啦的。”兩個娃還是說不遠瞭。大傢直走到下午四點多,才見一個莊子在一片紫竹林後露出頭來。娃才說,過瞭這個莊子就到瞭。
也的確是過瞭莊子就到瞭。可到瞭地方,幾乎沒有一個人再動彈得瞭。一打問,從鄉政府爬到這架山垴上,整整三十裡地。那位聯系戲的年輕人,嚇得連連賠著笑臉,說鄉親們的確是想看戲瞭,怪他把路途沒說明白。演員隊的幾個人,端直沖他喊叫起來:“小夥子,你這是詐騙行為,知道不?”有人甚至連揍他的心都有。是朱團長急忙阻擋瞭。大傢被安排到各傢各戶住下後,才知道,這個年輕人不僅騙瞭劇團人,而且也騙瞭村上的領導。其實,他既不是支書,也不是村主任。支書到區上參加商品觀念學習教育培訓班去瞭。隻有村主任在傢,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兩張皮”的不粘。據說,村委會馬上要改選瞭,這小夥子躍躍欲試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所以老主任就更是見不得這個“沒高沒低”“沒大沒小”“沒臉沒皮”的“怪貨色”瞭。年輕人沒跟他商量,就偷偷讓村裡人去把戲接回來瞭。戲箱都擺在小學門口瞭,才去給他打招呼,自是碰瞭一鼻子灰。老主任說他太膽大,這大的事,就敢做瞭主。雖說戲不要錢,可一下來瞭六十多張嘴,並且還要住一晚上,還要搭戲臺子,算是把天都戳下瞭窟窿。你個嘴上沒毛的貨,能成操起這大的事故來嗎?兩人大吵一架,然後村主任當眾宣佈,這事跟他半毛錢關系都沒有。說誰要捏著雞巴充六指子,讓誰充去,反正他管不瞭。隨後,他就關瞭門,上瞭鎖,說是去後山親戚傢瞭。年輕人既然把事惹下瞭,也就繼續朝前推著走瞭。好在,村裡人都想看戲,也都支持他。所以無論給誰傢安排人,都很順利。把人安到誰傢,誰傢就管飯。雖然山頂人傢,日子窮些,但也是盡著傢底往出騰。有的還煮上瞭臘肉呢。易青娥住的這傢,從廣播裡聽過《楊排風》,也知道易青娥,就越發地高興起來。最後甚至還殺瞭一隻雞,給她們幾個燉瞭,吃得一個村子都飄起香味來。倒是朱團長他們幾個老漢,住在一個傢裡,死氣沉沉的。給他們煮瞭一鍋紅薯,一吃,就連忙吹瞭燈,讓都麻利睡,說熬夜費油哩。
村裡一共有七十多口人。外村還趕來瞭一些看戲的。第二天上午,就把《楊排風》演瞭。誰知在開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來瞭。他是見全村人都服從瞭年輕人的安排,整整齊齊拿瞭板凳,坐在臺下看起戲來,就又頭不是頭、臉不是臉地對那年輕人說:“既然把事都弄到這份上瞭,我這個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說不過去。開演前,我恐怕得代表村上講幾句話,把人傢劇團謝忱一下。不能說我們村大小沒個規矩,誰都能出來拿瞭事。”年輕人就跟朱團長說,村主任回來瞭,要講話謝忱大傢呢。管音響的,給土臺子中間支瞭個話筒。主任撣瞭撣身上的灰土,就上去瞭。他剛朝話筒跟前一站,隻聽話筒“嗞兒”的一聲尖叫,嚇得他趔開瞭好幾步遠,嘴裡直嘟噥:“哎呀娘的個癟葫蘆子,嚇我這一跳好的呀!”他沒想到,這話都讓擴音器給擴出去瞭,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來。他又朝話筒跟前湊瞭湊說:
劇團同志們好!(音響又囂叫瞭一下)哎呀娘的癟葫蘆子,咋這愛叫喚的,嚇老漢一跳。(底下笑,他也笑)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劇團的同志要來,可我傢老母豬病瞭,去後溝找獸醫,回來給打瞭一針,豬才穩當些。中午說等同志們來呢,挨刀的婆娘,到後山去背洋芋種,回來的路上,把個胯子(大腿)扭瞭。我又去後溝裡接她。說晚上回來看同志們呢,親傢又捎話,說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訂婚的事。去親傢傢裡一折騰,就是大半夜。(音響又大叫瞭一聲)哎呀娘娘,這玩意兒咋比狼叫喚都難聽。(底下笑,他也跟著笑)剛說到哪兒瞭?噢,說到親傢瞭。這個親傢呀,你們都有親傢,親傢是天底下最難纏的親戚瞭。尤其是親傢母,是不是?(底下又有人笑)我說連夜回來看劇團的同志們呢,親傢母纏著走不利麼。球長瞭、毛短瞭的,就恨不得把我傢的門扇都抬瞭去,才肯嫁女呢。不說這些瞭,還是說看同志們的事。我說好瞭,今日個一大早,回來看同志們呢,你猜咋著的?你猜猜,你都猜猜……(底下就有人撂上話來:“猜死呢,都等著看戲呢。”)猜不出來吧?路上遇見瞭“一隻手”。“一隻手”你們都知道是誰吧?就是鄰村梁篾匠的兒子。不成器,到河溝炸魚,把一隻手炸掉的那個。你猜怎麼著?娃也學商品觀念呢。把他爺的老尿壺拾翻出來,偷偷拿到縣上一看,說是清代的,賣瞭三百塊。伢回來買瞭個錄音匣子提著,一路走一路放唱,都做的怪叫聲。他還弄瞭條能掃地的褲子繃在身上,褲腳就跟咱們樹上綁的那個喇叭叉子一樣,能多費好幾尺佈。(底下哄地又笑瞭)還戴瞭一副癩蛤蟆一樣的黑鏡子……(音響又是一聲銳叫)娘娘爺,你們劇團用的這是個啥玩意兒,把老漢魂都快要嚇出來瞭。縣上為啥讓戲來,讓戲來就是要搞商品觀念教育呢。商品,廣播裡說得清楚,凡有用的東西,都是商品。觀念是個啥呢?我也沒大聽清楚,廣播裡也講得黏糊拉索的。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要學會把東西變成錢,並且要一個勁地變。一個勁地變就是觀念瞭。但再變,恐怕也不能把你爺的老夜壺,都拿去變現瞭吧。你爺晚上在炕上咋尿呢?(大傢哄笑,音響也嗵嗵地炸響瞭幾聲)娘娘,還是離這個東西遠些好,快把我心臟撓攪出來瞭。總之啊,劇團同志們來瞭,戲來瞭,《楊排風》來瞭,這對我們當前的春耕春播,點洋芋、栽紅苕,都是很大的促進。尤其是對商品觀念教育活動,是促進得不得瞭的大促進!平常開個會,難纏死瞭,牛拽馬不拽、公到婆不到的,今天總算是竹筒倒豆子——一下都到齊瞭。我就順便開個會,把村裡當前的春耕生產佈置一下。下個月,上邊就要來檢查那個那個……商品觀念的事,我先說我們的臘肉問題……(底下就喊叫:“不要說瞭!”“我們要看戲!”“把×嘴夾緊!”……最後,有人還把磚頭都扔上來瞭。易青娥他們知道,劇團管音響的,也在不住地給他使壞。聲音把耳膜都能震破)哎呀娘娘,你們劇團這玩意兒,咋比我們村部的喇叭叉子還瞎些,聾子都能被你們嚇出病來。長話短說,反正有東西不賣,看來是不行瞭。沒臘肉賣瞭,打幾雙草鞋賣賣,我就不信,把你們的人還能丟到黃河裡去不成。(底下又喊:“我們要看戲,不看你!”“老臉難看死瞭!”“快滾下去,開戲!”)誰喊叫讓我滾下去?誰來?誰來?讓我滾,還輪不到你喊。真的是要變天瞭?還沒變麼。會還沒開麼。這戲,我要真的不讓演,那“鬧臺”還就敲不起來呢。咋的,耐不住瞭?這豹子溝垴啊,還不定誰說瞭算呢。好瞭,不說瞭。現在我宣佈——開戲!
戲演到一半的時候,突然下起雨來,有人就建議,是不是把戲“夭”一些。“夭戲”,在行當裡,就是誰傢要是招待不好瞭,或者遇見大風、雨雪天氣瞭,揀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讓觀眾基本能看懂就行。隻要不是老戲迷,一般也是看不出來的。到豹子溝垴來,本來大傢就累,一晚上又有沒睡好、沒吃好的。現在又下起雨來,自是有很多“夭戲”的理由瞭。可這一切,其實都掌握在司鼓與主角手中。易青娥她舅沒有要“夭戲”的手勢。易青娥看大雨下著,沒一個退場的,就想到自己小時跑十幾裡路看戲的事:哪怕下著雨,下著雪,雙腳凍得跟發面饃一樣,仍是生怕戲短瞭,戲完瞭。唱戲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來瞭。她就堅持著,硬是渾渾全全地把整本戲撐下來瞭。舞臺頂上的篷佈,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臺上潑灑著,把土臺子沖得溜光溜光的。好幾個演員都滑倒瞭。有的就把難度稍大些的動作,自然減掉瞭。可易青娥雖然幾次滑倒,但始終堅持著導演最初的要求。底下觀眾就不住地給她鼓掌、喊好,直到她完成最後一個動作。豹子溝垴村雖然隻有七十幾口人,加上鄰村的,也就一兩百觀眾。可那天在雨地中,他們始終不變的坐姿,還有那響徹山坳的吶喊聲,幾乎影響瞭易青娥一生。她領悟到,唱戲是不能偷懶的。人可能在偷懶中獲得一點快活,但卻會丟掉更重要的東西,也會丟掉一生最美好的記憶。
那天,易青娥第一次獲得觀眾給她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準備給兒子娶媳婦用的,他竟然心甘情願地拿出來披給瞭她。老村主任說:
“我一生沒看過這好的戲,也沒見過這樣賣力的演員。我們要都像易青娥這樣演戲、做事、實誠,豹子溝垴的日子,早都過到人前去瞭。可惜我們一直都在擺花架子,把好日子折騰完瞭。”
接他們去演出的那個年輕人,帶著村裡幾十號人,一直到把劇團送到下一個點。他們一路逢人便說順口溜:
看瞭《楊排風》,
沒酒沒肉也精神。
看瞭易青娥,
不吃不喝能上坡。
那天在路上,她舅跟她說瞭這樣一席話:
“娃呀,唱戲就要這樣,不能虧瞭自己的良心。為啥好多人唱不好戲,就是好投機取巧,看客下面。看著眼下是得瞭些便宜,可長遠,就攢不下戲緣、戲德。沒瞭戲緣、戲德,你唱給鬼聽去。‘夭戲’是喪戲德的事。尤其是‘夭’瞭可憐人的戲,就更是喪大德瞭。”
這一路巡演下來,一共進行瞭兩個多月,演瞭五十多場。走遍瞭寧州縣的山山水水。風裡雨裡,泥裡水裡,再苦再累,易青娥都沒“夭”過戲。也沒降低過任何演出標準。她的演技,她的風采,她的藝德,她的美貌,就被一傳十、十傳百地,傳得到處都是。幾乎每到一處,都有人把她圍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還得派出所出面維持秩序。每演一場,也都有人給她披大紅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幾床。在她最後回團的時候,竟然收獲瞭七十多床。她給去的人,每人都分瞭一床。縣上也是表彰,說劇團為商品觀念教育活動立瞭功。書記、縣長高興,還給團上每人發瞭一身演出服呢。
緊接著,全區要進行會演。團上又佈置瞭另一本大戲《白蛇傳》。
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無懸念地分給易青娥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