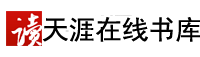毛澤東上井岡山,為中國革命找瞭一條符合實際的道路,但是這個起端沒有任何人褒獎,得到的反而是最嚴厲的處分。毛澤東通過艱辛摸索,開創瞭一條完全獨立的中國革命道路,不但獨立於敵人,而且獨立於友人;不僅政治獨立,而且經濟獨立。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在內外幹擾中取得輝煌的成功?蔣介石找過五個原因,但終生也沒有弄明白。克洛澤把所有原因歸結為一個最終的“運氣”,也沒有替蔣弄明白。回答者隻有毛澤東。
12.毛澤東如何步步探索正確的革命道路
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的“心境蒼涼”到八七會議後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鬥爭,毛澤東通過艱辛摸索,開創瞭一條完全獨立的中國革命道路,不但獨立於敵人,而且獨立於友人;不僅政治獨立,而且經濟獨立。事實證明,這條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最終獲得勝利的最主要的基礎。
當別人都還認識不到建設蘇區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的時候,毛澤東為什麼能夠找到這樣一條道路呢?並不是說這條道路原來就存在於領袖的頭腦之中,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革命生涯中一個艱辛摸索的過程。
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同志當時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心境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還並沒有非常明確地認識到走這樣一條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1927年八七會議,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思想開始比較成熟瞭。八七會議之前我們要註意一個重大的背景,八一南昌起義發生瞭,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通過自己的武裝打響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在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毛澤東第一次提出瞭石破天驚的理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到瞭1927年9月29日三灣改編,毛澤東提出支部建在連上。再到1927年年底井岡山鬥爭提出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實施工農武裝割據。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脈絡和發展的鏈路,這個過程在當年就已經論證瞭,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毛澤東對“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最後奪取城市”道路的探索,並不是胸有成竹:我早就有這個思想,上瞭井岡山,我就是為這個東西而來的。不是的。當初上井岡山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打長沙打不下來,隻能上井岡山,上瞭井岡山怎麼辦?和井岡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隊伍會合。那怎麼奪取未來的勝利呢?
井岡山地處偏遠,秋收起義的隊伍主要是湖南的農軍和留洋的學生,有一小部分武昌國民警衛團,力量很弱,再加上井岡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部隊,這兩個力量混合在一起,戰鬥力還是非常弱的。而且在當時的情勢下,這支力量不被任何人看好,共產國際根本就不知道在井岡山還聚集瞭這樣一股力量,更不可能想到這股力量最後能夠顛覆中國所有白色政權,奪取全國政權,這在當時而言,是任何人都無法想象的。
中國革命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我們先是政治獨立,最終保障政治獨立的是經濟獨立。經濟獨立的根源在哪裡呢?就是建立廣泛的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各個蘇區一起來,中國革命有瞭自己的雛形。毛澤東同志開創瞭這條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使中國革命有瞭立足的最主要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訪問蘇聯,見斯大林的時候,周圍的人都沒有想到,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我是長期受排擠打擊的人,有話無處說。”東方兩位革命巨人會見,何等非同一般的場所,毛澤東為什麼這麼說呢?長期沒有按照共產國際交代的那一套去做,走瞭中國的獨特的革命道路,這是獨立自主帶來的艱難曲折。毛澤東同志講瞭這些話之後,斯大林回答:“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這是一般公理。”
斯大林這位深刻改變瞭20世紀國際政治走向的歷史巨人,在勝利的中國革命面前,也十分坦然地承認瞭中國革命的成功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們中國共產黨人勝利瞭,那麼你們所選擇的方針、路線、政策就是對的,就是不受指責的,而我以前的指導就是有問題的,這是我也承認的。
13.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上)
在講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之前,我先講一件發生在我身邊的事。
我們國防大學有個國際問題交流班,這個國際問題交流班裡世界各國軍官都有,美國的、英國的、法國的、澳大利亞的、日本的,世界各國的軍官在一起除瞭學習交流,就是在國內考察。我記得我們當時參觀考察的第一站是山東地區,先看曲阜,就是孔子的故鄉,再到惠民,看孫子的故鄉,然後參觀青島著名的企業。
第一站參觀完後,西方幾個國傢的軍官提出一個請求,他們說:“你們的參觀項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都是安排給我們看的,我們能不能看自己想看的?”這是個很好的建議,我們離開山東,一到上海,就把原定安排全部取消瞭,大傢自由活動,交流班裡的中國軍官和幾名外國軍官結成小組,想看什麼地方就去什麼地方。
我當時負責為一名法國軍官和一名德國軍官帶隊,三個人組成瞭一個小組。從錦江飯店走出來,我就對法國軍官和德國軍官說:“今天時間都在我們手裡,你們說我們看什麼地方,我們就看什麼地方。”法國軍官首先建議,他說:“我們今天能不能看看中共‘一大’會址?”他的建議嚇瞭我一跳,我覺得我們今天很多中共黨員到瞭上海都很難想到要看中共“一大”會址。這位法國軍官剛到上海參觀,就要看中共“一大”會址,我立即答應。
這個法國軍官叫路易,在去中共“一大”會址的車上,我問路易:“你怎麼想起要看中共‘一大’會址呢?”路易興奮地說道:“中共‘一大’會址在當時是法租界呀,我們知道當時你們共產黨很危險,到處有人在追你們,抓你們,要殺你們,法租界很安全,你們在法租界召開瞭中共‘一大’,成立瞭中國共產黨,你們中共現在取得這麼大的成績,不要忘記我們法國人啊。”
他這麼一說,我才知道為什麼他要看中共“一大”會址。實際上他要看的是他們法國當年對中共“一大”作出的貢獻,就是說,是他們法國給我們中共提供瞭成立的地點。我對路易說:“路易,你到瞭中共‘一大’會址就知道瞭,你還得向我們道歉呢。”他感到非常吃驚,為什麼要道歉?我說:“你去中共‘一大’會址看看就知道瞭。”
我們在中共“一大”會址參觀,參觀到最後,當路易瞭解瞭中共“一大”會議的整個過程,他臉上的自豪感就消失瞭。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開,但並不是說就受到瞭法租界的保護。當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學生,沒有地下鬥爭經驗。會議開到五分之四時,突然有個人闖進來,闖進來後連忙說,走錯瞭,又把門拉上走瞭。年輕的代表們當時沒什麼經驗,以為真是有人走錯瞭門,大傢繼續開會。幸好當時參加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是個有著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荷蘭共產黨人,他當即提出不行,這個地點已經暴露瞭,立即轉移。馬林此語一出,代表們剛開始還有所猶豫,但新生的中共,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意見,在當時情況下是具有上級指示意思的,於是大傢立即轉移,決定把剩下的會議改在嘉興南湖召開。中共“一大”代表剛轉移不久,法國巡捕就沖進來抓人瞭。
我對路易說:“你好好看看,法國巡捕沖進來抓人,你說我們黨成立要感激你們,我說我們新生的共產黨差點兒被你們一網打盡瞭。”他說:“哎喲,還有這個事,我們真應該向你們道歉。”
從中共“一大”會址出來,我問那位德國軍官,“現在該你建議去看什麼地方瞭?”沒想到這位德國軍官提議去的地方,其潛在目的竟和法國軍官如出一轍。他說:“我們能不能看看孫中山故居,孫中山是中國革命最早引進德國顧問的,你們中國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國建設發展成這樣,不要忘記我們德國顧問曾經在這個過程中對你們作出的貢獻。”
通過這兩件事,兩個外國人,兩位外國軍官——他們後來都分別當瞭德國和法國的駐華武官——對我們黨和我們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認可的。但我們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們黨沒有取得這樣大的成就,如果我們失敗瞭,如果我們垮臺瞭,還會有人認可我們嗎?顯然,那位法國軍官絕不會以中共在法租界成立為榮,那個德國軍官也絕不以孫中山最早聘請德國顧問為榮。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瞭馬列主義,送來瞭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佈爾什維克黨人最後占領冬宮之前,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還不得不躲藏在俄國與芬蘭交界的拉茲裡夫湖邊一個草棚裡,離武裝起義隻剩下不到20天,才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即聖彼得堡)。
後來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基本上都是掃蕩法西斯德軍的蘇聯紅軍幫助建立的。當蘇聯的支持——特別是以武裝幹涉為代表的軍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墻便像一支廉價的雪糕那樣融化掉瞭。
越南、朝鮮,基本上大同小異。古巴的卡斯特羅遊擊隊也是在先奪取政權之後,才建立政權的。格瓦拉在南美叢林中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捉迷藏時,也沒有首先建立政權。
不是列寧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羅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沒有那種可能。
為什麼偏偏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
193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18年,毛澤東就在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之前,星羅棋佈的紅色政權已經在白色政權周圍頑強存在,並有效地履行一個政權的全部職能瞭。
為什麼在中國能夠如此?
全世界沒有哪一本《百科全書》能夠詮釋這個問題。
1975年蔣介石剛剛去世,美國作傢佈萊恩·克洛澤就出版瞭一本書The Man Who Lost China。書名就不大客氣,翻譯為《丟失瞭中國的人》。書中說:“對蔣介石的一生進行總結,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傢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他的運氣糟糕透頂。”
蔣介石數十年慘淡經營,竭力奮鬥,僅僅被歸結為“運氣”二字,克洛澤過於輕率。
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人的願望終生不改。十年內戰時期有“兩個星期”理論,解放戰爭時期發展為“三個月”理論——“三個月消滅關裡關外共軍”,兵敗臺灣後又有“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一輩子生活在撲滅燎原烈火的夢境之中。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在艱難困苦中頑強存在?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在白色恐怖中迅猛發展?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在內外幹擾中取得輝煌的成功?
蔣介石找過五個原因,但終生也沒有弄明白。克洛澤把所有原因歸結為一個最終的“運氣”,也沒有替蔣介石弄明白。
回答者隻有毛澤東。
14.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下)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早在1928年就作出瞭解答。
1928年10月,毛澤東寫於井岡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充分回答瞭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後來《毛澤東選集》四卷中一篇我認為非常關鍵的文章。隻有真正地認識到你腳下這塊大地的特點,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你才能真正完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
毛澤東是怎麼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
如果不看毛澤東是怎麼破解的,我們自己先破解一下,自己先問一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我們今天把它作為一道考題來回答一下,一般會怎麼回答?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指引;第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
第三,工農紅軍的英勇奮戰;
第四,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還可能第五、第六,這些都是標準的模式化的答案。
當我們按照這種標準的模式化的方法回答完之後,翻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文章看一看,就能夠明白,毛澤東當年如果按照我們今天這麼回答,我估計中國的革命是不一定能搞得成的。
那麼毛澤東是怎麼破解的?
毛澤東全面分析瞭中國社會的特質,他在這篇文章中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
毛澤東所講的獨特原因和相當的條件又是什麼呢?毛澤東說,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傢,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隨另外一種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這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最為關鍵的一條——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這也是毛澤東對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而列的五條理由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其他四條都圍繞這一條展開。
蔣介石在回答為什麼“赤匪”能夠有現在的猖狂時,也列瞭五條理由。在五條理由中,他認為“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是根本的一條。
毛澤東的五條理由中,“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是根本的一條。
毛澤東的認識之所以深刻,就在於他牢牢地根植於腳下的土地。
蔣介石在中國實施最嚴厲的白色恐怖,毛澤東卻在這最嚴厲的白色恐怖下,在各個實行白色恐怖的政權連年混戰中,為中國共產黨人找到瞭最廣闊的發展天地。
如此,我們可以看,後來革命發生的情況,我們各個蘇區,湘鄂贛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川黔蘇區等都是在白色政權之間的接合部,這就是毛澤東講的奇怪現象,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給中國革命提供瞭一個充分發展、發育、成長的空間。
中央蘇區就是廣泛利用瞭蔣桂戰爭、蔣馮閻戰爭獲得大幅度的發展。
紅軍長征,就是充分利用瞭白色政權之間的矛盾,在紅色政權失去瞭根據地之後萬裡長征仍能夠堅持下去。
這就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特質的充分掌握。
15.軍閥白崇禧因何為紅軍閃開一條路
中國工農紅軍萬裡長征的開始,並最後得以存活和發展,就是充分利用瞭“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蔣介石與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湖南軍閥何鍵、貴州軍閥王傢烈、雲南軍閥龍雲和四川軍閥劉湘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
長征出發通過前三道封鎖線就是紅軍與陳濟棠達成的秘密協議,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之戰,紅軍打得非常慘烈,損失過半。後來,我們很多著作中描繪瞭敵人如何兇殘,我軍如何英勇,當然這些都是客觀情況,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隱含在歷史帷幕後面的客觀情況,就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為我們讓開瞭湘江。
本身紅軍過湘江是非常困難的,到達湘江前,廣西白崇禧的軍隊由南向北,湖南何鍵的軍隊由北向南,已經把湘江完全封死。按常理,紅軍不可能通過這樣的封鎖線,可是在紅軍大隊人馬到湘江之前,白崇禧突然間調整戰線,把封鎖湘江的桂系軍隊的南北戰線陡然調整為東西戰線。他這一調整,湘江一下閃開瞭一個百餘裡的缺口。白崇禧為什麼突然間閃開這個口子?白崇禧在他桂系的高級軍官會議上講話,他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如果把湘江完全堵住,紅軍過不瞭湘江,必然掉頭南下進入我廣西,紅軍進入廣西,中央軍就要跟進廣西,中央軍在解決紅軍的同時把我桂系也就解決瞭,所以不如留著朱、毛,我們戰略回旋餘地還大些,我們現在是既要防紅軍,更要防中央軍。”
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這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那麼白崇禧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港澳臺一帶流行一種說法:中國有三個半軍事傢,兩個半在大陸,一個在臺灣。
在臺灣的這個就是白崇禧。
1928年,國民黨行政院院長譚延闓特寫有一副對聯贈白:“指揮能事回天地,學語小兒知姓名。”從白崇禧在陳濟棠面前對紅軍突圍時間和方向的料算,人們就可知道,不隻是共產黨的傑出軍事傢們才可以被稱做用兵如神。
1919年白崇禧任桂軍模范營連長,赴左江流域剿匪。廣西因為連年沿用招安政策,結果匪勢日張,形成“賣牛買槍”、“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局面。模范營招安招到土匪200名,白崇禧力主將其中的80名慣匪就地槍斃,以絕後患。廣西軍閥陸榮廷自己就是被招安的土匪出身,聞訊大怒,堅決不許。
白主意已定,獨斷專行,堅決斃掉瞭這80名慣匪。
此後,廣西對土匪的招安政策,改為進剿政策。
白崇禧這種秉性,在後來和蔣介石的關系中多次表露出來。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則是蔣、白配合的高峰。蔣在上海下定“清黨”決心,白則出任上海戒嚴司令;蔣發表《清黨佈告》《清黨通電》,白則在上海用機關槍向工人隊伍掃射。當時莫斯科百萬人大遊行抗議上海的白色恐怖,在“白”字下面,特地註明是白崇禧。
高峰之後,便是下坡瞭。而且因為成峰太陡,所以下坡也很陡。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僅4個月,白崇禧就與何應欽、李宗仁聯合,迫蔣第一次下野。後來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馮閻大戰、寧粵之爭,隻要是反蔣,就少不瞭白崇禧的身影。
白反蔣,蔣同樣反白。
1929年3月唐生智東山再起,白崇禧在北方無法立足,在一片打倒聲中化裝由塘沽搭乘日輪南逃。蔣介石獲悉,急電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著即派一快輪到吳淞口外截留,務將該逆搜出,解京究辦”。
蔣介石必欲除之而後快之心情,溢於言表。
後來虧得熊式輝的秘書通風報信,白崇禧方得以逃一命。
白、蔣關系是民國史上的一隻萬花筒,戰場上同生共死的關系瞬間就變成兵戎相見的關系,政壇上相依為命的關系眨眼就轉為你死我活的關系。
但蔣介石那個龐大的湘江追堵計劃,還是必須用白。桂軍戰鬥力極強,又有白崇禧的頭腦,很可能要唱主角。
白崇禧傾桂軍全部兩個軍於桂北邊境,以第十五軍控制灌陽、全縣(今全州縣)一帶,以第七軍控制興安、恭城(今恭城瑤族自治縣),自己也帶前進指揮所進至桂林,彈指之間,撒在湘江一帶的大網形成。桂軍完全一副在全、灌、興之間與紅軍決戰的架勢。
但白崇禧還多瞭一個心眼兒。他在調動大軍的同時出動空軍,名曰偵察紅軍行蹤,實則偵察蔣軍的行動。與蔣打交道多年,他太瞭解此人瞭,所以一直懷疑中央軍想借追蹤紅軍之機南下深入桂境。桂系的主要原則依然是防蔣重於防共,對紅軍“不攔頭,不斬腰,隻擊尾”,讓開正面,占領側翼,促其早日離開桂境。
臺灣《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記載,1934年11月17日,“白崇禧赴湘桂邊佈置防務”。
他不是去佈置戰鬥的,而是去佈置撤退的。
白崇禧原來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陣形,恰似一扇在紅軍正面關閉的大門。現在突然間被改為以湘江為立軸的東西陣形,似大門突然打開。尤其是全、灌、興三角地帶之核心石塘的放棄,更是令千軍萬馬、千山萬壑中出現瞭一道又寬又深的裂隙。
據湘軍記載,桂軍放棄全、灌、興核心陣地的日子是1934年11月22日。
此時紅軍前鋒距桂北已經很近。
完成這些佈置後,白崇禧才帶著劉斐去會劉建緒。劉建緒與白崇禧握手時,以為湘江防線業已被湘、桂兩軍銜接封閉,未料想恰是此時,桂軍那扇大門卻悄悄敞開瞭。
今天披露瞭蔣介石的日記,在蔣介石在日記裡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屠殺共產黨之前,要不要和共產黨翻臉,他頗費躊躇,十分猶豫,因為他跟共產黨翻臉,跟共產國際翻臉,勢必要影響蘇俄對中國北伐的武器和資金的援助,所以他猶豫再三,拿不定主意。最後,據今天放在美國胡佛研究所的日記記載是“勉強聽取瞭白兄的意見”,就是白崇禧力主跟共產黨翻臉,堅決要求屠殺共產黨人,所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瞭1934年,湘江之戰的時候,白崇禧在湘江放一個缺口,他不是為瞭紅軍,他是為瞭他自己,為瞭保住桂系。毛澤東說,我們隻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持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瞭。
毛澤東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是說是在任何的草原點個星火都能燎原的,他講的是在中國這塊草原點個火可以燎原,但別的地方就不行,為什麼呢?我們在前面講過,馬克思、恩格斯最希望的德國革命始終沒有發生,列寧、斯大林寄予很大希望的日本革命也沒有發生,而從來不被人看好的中國革命卻發生瞭,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就是因為有瞭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這就是中國革命的特質。
16.白色政權之間的鬥爭與分裂
紅軍過湘江,充分利用瞭蔣介石與桂系之間的矛盾。白崇禧在湘江邊為紅軍讓開一個口子,放紅軍過江,他做這些文章,也是很危險的,臨戰突然調整防線,這是難以交代的。
但白崇禧不愧為小諸葛,他當時給湖南軍閥何鍵發瞭個電報,說,紅軍有大規模進入廣西態勢,我要全力防范廣西,空出的戰線請兄速派兵填補。
何鍵一看電報就火瞭,這戰線在你廣西境內,你空出這麼大的范圍,我的兵力使用已盡,我怎麼幫你填補?
白崇禧為瞭補救,他又給蔣介石方面做瞭些工作,當時蔣介石通過空中偵察,已經發現桂系在湘江閃出瞭一個缺口。蔣介石嚴令指責白崇禧。蔣介石在電報中仍稱白崇禧為兄:兄做出此等事情,如果紅軍得以脫逃,兄將是千古罪人。
關鍵時刻,白崇禧為瞭應付蔣介石,他不得不打一下,所以當紅軍的後尾通過湘江的時候,白崇禧還是發動瞭攻擊。
即便是在紅軍過湘江隊伍還剩兩三天的時候,白崇禧的桂軍發動瞭攻擊,也給紅軍的後尾造成瞭不小的傷害。
但是給紅軍造成最大傷害的,還是何鍵的湘軍。
其實白崇禧當時發動攻擊的主要目的還是驅趕,把紅軍趕出去。當時桂系內部開會,還有一個擊大尾,還是擊小尾的問題。就是紅軍通過湘江的時候,是在紅軍隊伍剩四天到五天,桂系發動攻擊,還是剩兩天到三天,或者是一天到兩天發動攻擊。這裡邊牽涉到桂系可能承擔多大的戰爭任務的問題,後來白崇禧決定,為瞭避免桂系更大的損失,剩兩天的時候發動攻擊,不要打大瞭,打大瞭桂系傷亡也大。
這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盤算。
那麼當地方軍閥這麼盤算的時候,蔣介石就沒有做這樣的盤算嗎?蔣介石也做瞭這樣的盤算,當時追擊紅軍的中央軍,兩個中央軍的縱隊,吳奇偉縱隊和周渾元縱隊都收到瞭蔣介石發來的電報,蔣介石要求追擊縱隊與紅軍隊伍保持一天到兩天的行軍距離。
蔣介石也在驅趕。
蔣介石這種驅趕式的追擊,不要做大規模作戰的追擊,其意圖已經很明顯瞭。
蔣介石的想法是什麼呢?蔣介石曾說,中國自古以來,未有(流寇)能成大事者。蔣介石認為紅軍已成流寇,脫離瞭根據地,已經成不瞭事瞭。他還講,李自成就是流寇,滅亡瞭;石達開就是流寇,滅亡瞭。今天紅軍也是流寇,滅亡是遲早的事情,所以說不用那麼著急,做驅趕式的追擊,把紅軍追到哪裡,就把地方軍閥解決到哪裡。
追到廣西,解決白崇禧。
追到貴州,解決王傢烈。
追到雲南,解決龍雲。
這就是蔣介石的盤算。
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白色政權之間的分裂,其實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這個“心眼”。互相保存實力,互相盤算對方,因此形成瞭非常大的裂痕,這給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瞭一個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