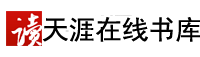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宋太祖•趙匡胤
一、銅鈴
趙不尤讓墨兒留在章七郎酒棧,繼續查尋董謙蹤跡,自己隨著萬福一起進城,趕往皇城。
途中,萬福邊走邊解說,他背的文書袋裡似乎有個銅鈴,隨著步履一動一響:“宮中冰庫這樁命案是三月三十一那天發覺,死者是冰庫中一個老吏,名叫嚴仁。已經過瞭幾天,仍未查出真兇。卑職將才帶仵作去汴河灣客船上查看那具屍首,才發覺兩案恐怕有關聯。死者屍首都在一隻打開的木箱中,面色青黑、嘴唇烏紫,都是中毒而亡。兩案都與梅船案相關。趙將軍您已推斷,清明林靈素身後童子所撒鮮梅花,恐怕是預先在宮中冰庫中凍藏的。汴河客船這案子,又是紫衣人董謙——”
“客船上那死者身份可查出來瞭?”
“是耿唯。”
“耿唯?”趙不尤極為吃驚,“他不是已經離京赴任去瞭?”
之前,東水八子決裂,簡莊等人哄騙宋齊愈去應天府,應天府那空宅地址便是耿唯提供。
“耿唯的確離京瞭。卑職前幾天才想起來,清明那天,虹橋發生那樁異事前,卑職提瞭一壇酒出城,見城門外有幾個人在護龍橋上送行,送的那行客便是耿唯。他戴瞭頂風帽,騎瞭頭驢子,帶瞭幾個仆從。卑職由於著忙,便沒介意。不過,回想當日情形,耿唯的確是離京瞭。他由一個閑職升任荊州通判,正該遠遠避禍,不知為何,又返回京城,竟死在那隻船上。”
趙不尤低頭默想:這兩樁案子看來的確都與梅船案相關,不知這梅船究竟藏瞭多大隱秘,命案至今仍延綿不斷。冰庫老吏恐怕正是藏凍鮮梅花之人,他和耿唯相繼死去,自然是被滅口。他們死狀如此詭異,一是為遮掩,二則是繼續借妖異怪象來惑人。但死在木箱中,究竟是何用意?
萬福繼續說:“那天清晨,冰庫老吏被發覺死在宿房裡,趴在靠窗墻角邊的一隻書箱裡,身體已經僵冷。門從裡頭閂著。皇城裡的房舍門閂不似民間,並非木閂,而是帶鎖扣的銅閂,從外頭根本無法開關。那宿房隻有一扇窗,在房門左邊,那窗扇是死扇,打不開。”
“最先發覺的是什麼人?”
“當時院裡有兩人,一個是新任庫官,一個是冰庫小吏。小吏喚不應老吏,新庫官才抬腿一腳踢開瞭宿房門。小吏先奔進房中,新庫官隨即也跟瞭進去。新庫官和董謙等人同為上屆進士,待闕三年,才得瞭這個職任。那天是他頭一回去冰庫,他先到的冰庫,當時院中並無他人。不過,他應該不是兇手。顧大人親自問訊過,他言語神色之間毫無疑色。而且,堂堂進士,朝廷官員,想必不會冒這最大嫌疑之險,去毒殺一個老吏。”
“那小吏呢?”
“小吏名叫鄒小涼。冰庫裡常日隻有他和老吏兩人,鄒小涼又一直替老吏煎茶煮飯,自然極好下手施毒。前一天傍晚,他替老吏煮好飯才離開。不過,據仵作查驗,和耿唯相同,那老吏並非服毒而亡,而是被毒煙熏死。那個新庫官也說,剛進宿房時,嗅到瞭一陣怪異香氣。”
“窗紙可有破洞?”
“窗紙是今年正月才新換的。破洞隻有一個,是那天喚不應老吏,小吏才去窗邊,在窗戶左側舔破瞭一個小洞,朝裡窺望。此外,窗紙上連一道細縫都沒有。倒是那木箱有些古怪,據小吏說,裡頭原本裝的全是書卷。他們進去時,見大半書卷被挪到瞭箱子外。箱角書卷下壓著一樣奇怪物事——”
“什麼?”
“這個——卑職這兩天一直帶在身邊,卻始終未瞧出什麼原委——”萬福從袋裡取出一個銅鈴遞給趙不尤,“這個銅鈴放在書箱最底下角落裡,上面壓著些書。卑職查看那書箱時,將裡頭的書全都搬出來,才發覺這個銅鈴。”
趙不尤接過來細看,這銅鈴隻比拳頭略大,並非手搖鈴,而是掛鈴,頂上有個小環扣,外壁鏤刻道教符紋,在道觀中極常見。
萬福又說:“那個新庫官說,鄒小涼朝窗洞裡窺望時,他似乎聽到瞭一聲鈴鐺響,不知是否是那老吏還剩瞭一絲氣,動彈瞭一下,碰響瞭銅鈴⋯⋯”
趙不尤看不出這銅鈴有何異樣,搖瞭搖,聲響也和一般銅鈴相同,便還給瞭萬福:“那個小吏沒聽見那聲鈴響?”
“他說沒有。當時他正忙著喚老吏,恐怕是被自己聲響蓋過瞭。還有一樁古怪——將才卑職帶仵作去汴河那隻客船上查驗耿唯屍首時,發現他那隻木箱裡也有一隻銅鈴,和這隻一模一樣。”
“哦?”
“不知這銅鈴藏瞭何等隱秘?”
趙不尤卻猛然想起另一樁事,忙說:“看來冰庫老吏一案,你已查得極仔細瞭,我暫無必要再去。我得立即去見一個人——”
“什麼人?”
“武翹。”
二、袋子
陳三十二探頭探腦走近爛柯寺。
他是崔豪的朋友。昨天,崔豪尋見他,要他幫忙做一樁事。他沒問情由,便滿口答應。
前一陣,他那渾傢又生產瞭,請穩婆的錢都沒有,隻能由渾傢自己硬掙。陳三十二其他幫不上,拿瞭把銹剪刀,守在破床邊焦等。孩兒終於冒出瞭頭,卻卡在那裡,擠不出來。看渾傢疼得喊爹叫娘,幾乎要將下嘴皮子咬掉一片。他恨不得一剪刀將那孩兒戳死,再硬扯出來。最後,孩兒總算出來瞭。他慌忙去剪臍帶,可那剪刀左拐右撇,兩片刃死活咬不齊,掙瞭一頭汗,總算剪斷。
又是個女孩兒,已是第四個。三個大的守在門外,張著嘴等飯吃。人越窮瘦,嘴便越大,也越填不滿。如今又添瞭這張小嘴兒,不知拿什麼來喂大。
他正在犯愁,崔豪三兄弟卻來賀喜,拿出個佈包給他,讓他莫焦,好生養活一傢人。他接過來打開外頭的舊佈一瞅,裡頭竟是銀碗,一摞六隻。他驚得說不出話,再看那銀碗,裡頭光亮得月亮一般,外頭雕滿瞭纏枝花紋,細處細過發絲,卻彎彎繞繞,沒有一根亂的。他活瞭三十來年,從沒摸過這麼精貴的物件。他以為崔豪在耍弄他,但看崔豪三人神色,的確是誠心幫他。他抱著那六隻銀碗,竟哭瞭起來。
崔豪三人走後,他才疑心起來。雖說認得的力夫中,崔豪是最豪爽誠懇的一個,最愛幫人。但他也賣力為生,哪裡得來的這六隻銀碗?莫不是偷來的?怕不會惹上禍事?但轉念一想,怕啥?再大的禍能大過孩兒餓死?若真是偷來的,得趕緊脫手才是。
他忙拿瞭一隻,拿佈包起來,去附近一傢解庫典賣,那掌櫃果然疑心他是偷來的,說隻肯出三貫錢。他一聽,心裡驚喚瞭一聲。他雖知這碗一定值價,卻不料被壓瞭價,竟還能值三貫。他頓時得瞭計,包起來就走,又連問瞭許多傢,最高的竟出瞭六貫錢。他每個月就算天天能尋到活計,也掙不到這許多。他將六隻銀碗都賣給瞭那傢,大半年不必再愁飯食。
他從未受過這等恩德,這回崔豪有事要他相幫,便是斷條腿,也不能推辭。可聽崔豪細說瞭要做的事後,他心裡又開始犯疑。這事聽來雖輕巧,但古古怪怪,莫不是有什麼禍患?崔豪先拿那六隻銀碗,莫非是個鉤子,先釣上我,再行大事?崔豪說這事是幫一個恩公,什麼恩公這等鬼鬼祟祟?他們做這事,恐怕能賺到六百隻銀碗⋯⋯他心裡翻翻倒倒,不知繞瞭多少轉兒。可聽崔豪說,若做得好,往後一定好生酬謝,他面上更不好流露,隻能點頭應承。
崔豪走後,他越想越疑,越疑越怕。他渾傢一邊奶孩兒,一邊說:“這事恐怕做不得,你若有個閃失,俺們娘女幾個咋個活呀。你趕緊將那些錢還給崔豪,已經花用掉的那幾貫,俺們慢慢還他。”陳三十二聽瞭,反倒硬瞭起來。他一向有個主見,但凡婦人傢的主意,一定是錯。就如他這渾傢,原本是鄉裡三等人戶的女兒,若好生嫁個當門當戶的人傢,便是生八個孩兒,也養活得過。她卻偏偏對他生瞭情,跟著他偷逃離傢,來到這汴京城,住在這城郊一間破土房裡,日日苦挨。
他回過頭細想,自己欠瞭崔豪這一樁人情,無論如何得還,否則心裡始終難安生,也難在崔豪面前抬起頭說話。另外,崔豪這人大抵還是信得過,我替他去做這事,就算喪瞭命,崔豪想必不會不管顧我妻女。他若賺六百隻銀碗,少分幾十隻給我渾傢,也夠她們娘女幾年過活。那時大女也該出嫁瞭,她生得似她娘,將來必定是個小美娘,聘資少說也得幾十貫。這又夠把二女養大,隻可惜二女樣貌似瞭我。不過,滿京城多少光桿兒漢,女孩兒生得再不好,也是寒冬臘月間的嫩蔥,還愁嫁不出去?我傢沒兒,不如贅個婿進來。哪怕窮些,有氣力,人心正便好。我不在瞭,她們娘女必定受人欺辱,有個漢子來頂門才好⋯⋯他越想越遠,忽而傷悲起來,不覺想出淚來,忙扭過頭,用袖子趕緊抹幹。
第二天,他偷偷藏瞭把刀在腰間,照著崔豪所說,來到爛柯寺。
他是頭一回進這小寺。見裡頭靜悄悄的,沒一個人影。他頓時怕起來,轉身想逃,卻見一個小和尚從旁邊禪房裡出來,見瞭他,微微笑著,合十問訊:“院靜識性空,無我見來人。”
他沒聽懂,卻見小和尚一臉和善,心裡稍安,忙悄聲說:“我來取那東西。”
小和尚神色微警,又說瞭句:“我有百萬偈,問君何所答?”
這句正是崔豪交代的,陳三十二忙答:“囊盡三千夢,終究一袋空。”
小和尚又笑瞭一下:“禪客疑雲散,施主隨我來。”
陳三十二忙跟著小和尚走到旁邊一間禪房,小和尚提出一隻灰佈袋子交給他。袋口用細繩拴著,裡頭似乎是些書冊。陳三十二忙接瞭過來,有些沉。他背到肩上,回頭望瞭一眼,見小和尚又雙手合十,輕聲說:“揮手送客去,一帆凈風煙。”
陳三十二茫然點點頭,忙背著袋子離開爛柯寺,出瞭門,才想起崔豪說要慢慢走,莫要慌。他忙放慢腳步,滿心猶疑,一路走到護龍橋口,卻見崔豪正扒在橋欄邊,裝作沒見他。他也忙低下眼,轉身向東邊行去。一直走到虹橋,抬頭又見劉八站在胡大包的攤子邊,正吃著個大包子,裝作望河景。他低頭上橋,照吩咐,過橋後沿汴河北街,一直走到力夫店,再折到河邊,沿著岸又回到虹橋。下瞭橋,直直向南,經過十千腳店,一眼又瞧見耿五蹲在斜對面溫傢茶食店的墻根。他仍裝作沒見,折向右邊那條小巷,走到左邊第一個院門前,取出崔豪交給自己的鑰匙,打開瞭門鎖,走瞭進去,隨即閂上瞭門。
院子裡極安靜,他越發有些怕,小心推開正屋門,裡頭如崔豪所言,果然空無一人,但桌椅箱櫃都十分齊整幹凈,墻邊一架子書。屋中間方桌上擺瞭一副碗箸、一盆熟切羊肉、一碟薑辣蘿卜、幾張胡餅,還有一瓶酒,這是給他預備的飯食。
他不放心,又將其他四間屋子一一查看過,的確沒有人。他卻仍有些怕,輕步回到正屋,將那袋子放到門邊那隻櫃子裡,而後才小心坐到屋子中間那張方桌旁,手伸到腰裡,攥緊瞭那把刀子——
三、木雕
明慧娘透過廂車簾縫,偷望著梁興,不由得攥緊瞭腰間那柄短刀。
她已求得宰相方肥應允,梁興必須由她親手殺死。但宰相也叮囑過,眼下最要緊是找見那個紫衣人。清明正午,梁興闖到鐘大眼船上,自然也是為瞭那紫衣人。眼下,他一定在四處找尋,恐怕已經探到紫衣人蹤跡,跟蹤梁興,或許能尋見那紫衣人。明慧娘隻能暫忍。
她盯著梁興那健實後背,心裡反復演練。然而她從未殺過生,更莫說殺人。每想到刀尖刺入那後背,身心頓時抽緊,始終下不得手。她顫著手,不住恨罵自己,再想到丈夫盛力,淚水隨之迸湧而出。
遇見盛力之前,她似乎從未見過天光。她爹是浙江睦州的農戶,傢中隻有幾畝薄田,另佃瞭十幾畝地,才勉強得活。她上頭有一個哥哥,還有兩個姐姐。她爹嫌女孩兒白耗食糧,那兩個姐姐才出世,便都被溺死。她娘生下她後,她爹照舊要拎出去丟到溪裡。她娘哭著哀求,說這囡囡面目生得這般好,長養起來,至少能替兒子換一門親。她爹聽瞭,才將她丟回到她娘懷裡。
三四歲起,她便開始幫娘做活兒,撿柴、割草、生火、煮飯、灑掃、洗涮、養蠶、繅絲⋯⋯她爹卻從不正眼瞧她,除非吃飯時,隻要她略略發出些聲響,她爹頓時怒瞪過來,甚而將竹筷劈頭甩過來,令她活得如同受驚的小雀一般,隻要爹在,從不敢發出任何聲息。
長到七八歲,她的模樣越來越秀嫩,人人都贊她生得好。她卻越來越怕,知道這容貌是災禍。果然,村中漸漸傳出風言,說她爹生得歪木疙瘩一般,哪裡能養出這等嬌美女兒來?更有人私傳,她娘與那上戶田主有些首尾。穢語很快傳到她爹耳朵裡,她爹將她娘痛打瞭一頓,隨即拽著她,大步望城裡奔去。她不住地哭,換來的卻是巴掌和踢打。
進瞭城,她爹將她拽進一座鋪紅掛綠的樓店,她驚慌無比,卻不敢再哭。及至見到一個身穿彩緞的胖婦人叫人搬出一堆銅錢,一串一串地高聲數給她爹,她才明白自己被賣瞭。她爹將那些錢裝進帶來的空褡褳裡,背到肩上後,扭頭望瞭她一眼,那目光仍舊冰冷冷的,卻有一絲發怯。她原本慌怕之極,淚水流個不住,可一眼看到爹眼裡露怯,忽而便不怕瞭,生下來頭一回直直盯瞭回去。她爹慌忙低下頭,背著那錢袋快步出門,拐走不見,她的淚水也跟著停瞭。
後來,她才知曉,這是一傢妓館。那媽媽極嚴苛,每日命她學寫字、彈阮琴、唱曲子。略一出錯,便用纏瞭絹的鐵條抽打,那絹原是白色,早已變得烏褐。她在那妓館中,雖已笑不出,卻也不再哭。學這些,並不比在傢中苦累。她便用心盡力去練,挨的打也越來越少。
這妓館中還有幾個與她年紀相仿的女孩兒。那些女孩兒見她討得媽媽歡心,氣不過,便時時湊在一處為難她。她能避則避,能讓則讓,心裡並不計較記恨,更不去告訴媽媽。實在受不得,才還擊一二。那些女孩兒見她並非軟懦,便也漸漸消停,隻是合起來疏冷她。她更不以為意,自己並不希求友伴。越冷清,她心裡越安寧。
長到十二歲,媽媽叫她接客。是個中年肥壯鹽商,兩隻牛眼,一嘴黃牙。她早就預備好這一天,雖有些怕,卻仍照媽媽訓教的,淺淺笑著,點茶斟酒,彈琴唱曲,盡力不去看那張臉。夜裡被那鹽商按倒在床上,她閉緊瞭眼,咬牙挨著,痛極瞭,才發出一些聲息。雖然眼角滾下淚來,心裡卻沒哭。
第一回挨過,後頭便好瞭。每天她盡力坐在自己房中讀書,有客來,便去應付過。她不知哪一天才是終瞭,心中無所盼,便也無所念。
幾年後,一個漆園主愛她會讀書寫算,便花瞭三百貫,將她贖去做妾,替自己記賬。那漆園主傢中已有十幾個小妾,其中有幾個極尖酸狠厲,見她容貌生得好,又掌管起漆園賬目,都極妒恨,攛掇正室,時時刁難她。這些伎倆,她在妓館中早已慣熟,自己又絲毫沒有爭寵之心,便照舊敬而遠之、淡而化之。漆園主對她先還有嘗鮮之情,見她始終冰水一般,也漸失瞭興致。時日久瞭,那幾個小妾也沒瞭逗趣。她終歸清靜,每日算錄好賬目,便自在臥房裡讀書,活得古井一般。
就在那時,她遇見瞭盛力。
那漆園主是個蠻夯豪橫之人,並不顧忌男女內外之別。每年春夏割漆、秋冬出賣,都叫她去山上漆園一座棚子裡記賬。那些漆工全都畏懼園主,到她跟前報賬時,都不敢抬眼直視,她更是眼裡瞧不見人,始終冷冰冰的。那園主起先還常來盯看,見這般情形,更放瞭心,隻叫一個使女陪侍。
有一天,各坡的工頭都來交納生漆,算過錢數後,已是傍晚。她有些倦乏,便沒有立即下山,叫使女去燒水煎茶,自己坐在棚子裡歇息。當時正是初夏,她常日難得留意外界景物,那天看到夕陽下滿目新翠,忽而憶起幼年時和娘一起去山坡上割薺菜,山野光景便是這般鮮明。她娘那天臉上現出難得笑意,摘瞭兩朵地丁黃花插在她丫髻上,牽著她一路哼著鄉謠。她盡力回想,漸漸憶起那曲詞,不由得輕聲吟唱起來,腳也忍不住踩起拍子,腳尖卻忽然觸到一樣物事。
她彎腰一看,桌腳邊有個小佈卷兒,撿起來打開一看,不由得愣住:裡頭是一個小小木雕女子人像,隻比拇指略大,卻雕得極精細,眉眼都清晰如真。又塗瞭一層清漆,光潔瑩亮。最教她吃驚的是,那面容越瞧越酷似她。隻是,這女子似乎想起一樁趣事,嘴角微揚,面露笑意。
明慧娘自己從未這般笑過,盯著那小像,她不由得怔住。棚子邊響起窸窣腳步聲,那使女煎好瞭茶,端瞭過來。她忙將那小木雕藏進袖裡,再也無心看景吃茶,叫使女收拾好賬簿,一起下山去瞭。
回到臥房裡,她又忍不住拿出那木雕仔細賞看,恍然間,竟覺得所雕這女子是另一重人世中的自己。在那重人世裡,父疼母愛,傢境和裕,無須驚怕,不必冷心⋯⋯想著那個自己,她不由得也露出瞭笑。但心頭旋即升起疑雲:這是何人所雕?為何會丟在桌下?
在山上,除去使女,進到棚子裡的,隻有那幾個交漆的工頭。難道是工頭中的一個?她極力回想,卻猜不出是哪一個。
這之後,再到山上記賬,她開始細心留意,卻未能找出那人。半個多月後,有天記完賬,桌下又出現一個佈卷,裡頭仍是一個小小雕像,雕的依舊是她,隻是笑得越發歡悅。
她忙回想那天情形,隻有一個工頭數錢時,失手跌落瞭一串錢,俯身去撿瞭起來。那個工頭似乎叫盛力。
四、川藥
魯仁驅趕牛車,將張用載到瞭金水河邊一個小院裡。
寒食那天,一個中年漢子來到他藥鋪,瞧身形面相,年紀不過三十左右,鬢發卻已花白。那人說有件要緊事,將他喚到沒人處,壓低聲音說:“我知你兒媳屍首去瞭哪裡。”
他聽瞭,頭頓時一嗡,幾乎昏倒。
那人卻冷著臉,等他略略平復後,才又開口:“你得替我做一樁事。”
“什麼事?”
“捉一個人。”
“什麼人?”
“作絕張用。”
“這等事⋯⋯我⋯⋯我做不來。”
“殺人都殺得來——”
“你⋯⋯”
“莫要多話。綁瞭那人,堵住嘴,裝進麻袋裡,送到西城外十五裡,過演武莊遞馬鋪,金水河南岸有個小宅院,門前種瞭幾株大香椿樹。這是鑰匙,你將那人鎖到房裡後,在院門上插一根香椿枝。”
那人將一把鑰匙塞到他手裡,轉身便走瞭。魯仁愣在那裡,半晌都動彈不得。
他從未做過虧心事,兒媳之死已讓他日夜難安,如今竟有人以此來脅迫自己去做那等事。這時他才明白,兒時父母常叮嚀那句話:“人生在世,一步都差不得。差一步,便是千差萬錯。”
他想去官府自首,將全部罪過都攬到自己頭上。但一想,官府自然不會輕易相信,若是盤問起來,略有錯訛,便會牽扯出兒子。兒子如今時常癡癡怔怔,哪裡經得住審訊。
他千思萬想,想到瞭一人。那人是汴京三團八廂中的一個廂頭,這左一廂是他地界,手底下有上百個強漢無賴。魯仁也時常受這些人勒討錢物。前年,這廂頭的一個愛妾難產,落下息胞之癥,急需川牛膝和藥。京城各大藥鋪卻偏偏都缺貨。魯仁一個老主顧正巧運瞭一船川藥來,裡頭正有川牛膝。魯仁忙叫兒子急送瞭些給那廂頭,救瞭那愛妾的命。那廂頭封瞭一份大禮,親自來道謝,並說遇到難事,一定去尋他。魯仁卻哪裡敢去觸惹這等人,隻是唯唯點頭。
如今遇到這等煩難,為瞭兒子,他隻得去求那廂頭,又不敢將事情說透。那廂頭見他話語含糊,有些著惱,卻仍給他指派瞭一夥人。魯仁去見瞭那夥人,竟是幾個侏儒、一個啞子、一個跛子。他大失所望,卻再無他路,隻得將事情交托給那侏儒頭兒。沒料到這群侏儒竟做成瞭這樁事,雖說臨時反悔,多訛瞭三十五兩銀子,畢竟遠勝過自傢去動手。
前幾天,他瞞著兒子,已來這金水河邊尋踏過路徑,見那個宅子隻是尋常農傢小院,隱在幾株大香椿樹後,這一帶又極僻靜,左右並無鄰舍,他才略放瞭些心。這時天色已晚,路上也沒瞭行人,更不必擔心被人撞見。
隻是,這牛車雖是他藥鋪裡載貨的,他卻從未趕過。加之天黑,路又不平,磕磕絆絆,費盡瞭氣力,才算來到那院門前。他取出鑰匙,手臂酸累,顫個不住。半晌,才打開瞭鎖。他忙牽拽牛繩,將車拉瞭進去。
幸而張用一直在麻袋裡睡覺,一路都未發出聲響。他想起那人吩咐,得將張用的嘴堵起來,卻不敢解開麻袋。又想,是否該將張用搬進房裡去,可憑自己氣力,恐怕搬不動。再一想,牛車不能丟在這裡,還是得將張用搬下來。可萬一驚醒瞭他,嚷叫起來,如何是好?
他正在猶豫,忽見那麻袋動瞭動,隨即聽到張用在裡頭嘟囔:“餓瞭。”他嚇瞭一跳,沒敢應聲。張用卻提高瞭音量:“我餓瞭!”
他越發慌瞭,不知該如何阻止。今天出門時,他想著荒郊野外不好尋食店,倒是帶瞭幹糧和水,並沒吃幾口。但若拿給張用吃,便得解開麻袋,這萬萬不可。
“你姓魯?”張用忽然問。
他驚得頭皮一炸。
“你一身藥味,不是藥鋪的,便是行醫者。但這兩樣人,身上藥味都雜。你身上我能聞得出七種藥氣,一色盡是川藥,川芎、川貝、川烏、川羌活、川楝子、川椒、川樸硝⋯⋯汴京城獨賣川藥的隻有蔡市橋仁春藥鋪。將才你和那老孩兒論價,輕易便多掏瞭三十五兩銀子,自然不是那藥鋪雇的夥計,聽你聲音,年紀至少五十歲,你是那藥鋪的店主——”
魯仁聽得膽都要驚破。
“你連貨都不驗,自然是頭一回綁人。你一個小藥鋪店主,綁我做什麼?自然是受人指使。但你給那老孩兒付錢時,聽語氣,是自傢出錢,自傢做主,並不是靠這差事謀財,自然是受人脅迫,不得不為。你為何會受人脅迫?自然是短處被人捏住。何等短處能脅迫你來綁劫?勝過綁劫罪的,應該隻有殺人罪。你殺瞭人!”
魯仁急顫瞭一下,險些坐倒。
“不對⋯⋯人若是你殺的,被人脅迫做這等事,你心裡必定極不情願。人若懷瞭不情願,行事時自然負氣,極易遷怒。可是我聽你趕牛時,那牛不聽你驅使,你卻隻有焦急,並無氣怒。你自然不是疼惜牛,而是念著盡快完成這樁差事。你是心甘情願做這樁事。殺人者,不是你,而是你至親之人。父母?妻子?兄弟?兒女?我琢磨琢磨⋯⋯聽你說話舉動,處處透出些急切。拽牛時,也拼盡全力,似乎把性命搭上也在所不惜。世間恐怕隻有父母對兒女,才會這般不惜自己氣力、不顧自傢性命。另外,你這急切拼命裡,似乎還有一分熱望,做完這樁事,便能延續自傢性命一般。能延續你性命血脈的,唯有兒子。殺人的是你兒子,哈哈!你是在替兒子保命,對不對?”
魯仁渾身冰涼,抖個不住。
“脅迫你來綁我的,是不是銀器章?你傢藥鋪正和他傢院子相鄰,你兒子殺人,被他瞅見瞭?”
魯仁頭腦一嗡,像挨瞭一錘。
“你莫怕,這是你自傢的事,我不會告發你,更不會脅迫你。以你這米豆般小膽,你受的罪已遠勝過徒刑,更苦過殺頭。你那兒子恐怕也與你一般。我隻勸你莫再受人脅迫,做這些歹事。愧上添愧愧更愧,罪外加罪罪更罪。阿鼻地獄便是這般來的——好瞭,我不但餓,說瞭這些閑話,口也幹得灶洞一般瞭。你去給我尋些吃食來。吃飽喝足,我繼續在這安樂袋裡睡覺,等那人來取我。你也好放心尋你的解脫去——”
魯仁猶豫良久,還是從車轅邊取下水袋,過去解開瞭麻袋口⋯⋯
五、醫心
陸青行至新鄭門外,來尋王倫的另一好友溫德。
溫德年近四十,傢中世代行醫,他曾考過一回太醫,沒中,便丟瞭這念頭,在這西城腳開瞭間醫鋪。陸青走到醫鋪門前時,夜已深瞭,醫鋪門卻仍開著,裡頭透出油燈光。
溫德才給一個老者問過診、配好藥,那老者從腰間解下一個小綢袋,邊摸錢,邊傷老嘆貧。陸青看他衣著神色,並非窮寒之人,隻是慣於倚老貪討小利。溫德也瞧出他這心思,卻隻笑瞭笑:“都是尋常藥,您隨意付兩文錢就是瞭。”“兩文?怕是少瞭?”“不少,不少,比一文多一倍。”老者忙將抓出的一把銅錢塞回袋裡,果真隻拿瞭兩文出來。溫德笑著接過,隨手丟進桌邊的陶罐,送老人走到門外:“夜黑瞭,您仔細行路。”一扭頭,才發覺陸青,先是一愣,隨即瞇起眼笑道:“忘川?難得逸人出山,快請進!”
陸青抬手問過禮,才舉步走進醫鋪。裡頭三面排滿藥櫃,中間隻剩幾尺寬空處,又擺瞭張桌子,一椅一凳。陸青便在那圓凳上坐瞭下來。
溫德關好門,從桌上茶盤中提起一隻陶壺,倒瞭盞水遞瞭過來,湯色清白:“我那渾傢這兩日犯瞭春疾,已經去後頭睡瞭,爐火也熄瞭,便不給你點茶瞭。春宜護肝,這是熬的白菊葛根湯——”
陸青笑著接過:“溫兄隻醫身,不醫心。”
溫德微微一愣,旋即明白說的是將才那老者,便又瞇起眼呵呵笑起來:“我隻是半上不下一郎中,哪裡敢醫人心。連孔聖人都說,老來戒之在得。越老越貪,怕是人之常性,否則何必言戒?何況隻爭幾文錢,有何妨害?怕的是,老來貪占權位,不肯退閑,那便真如孔聖人所言,老而不死謂之賊——對瞭,那楊戩是你⋯⋯”
楊戩死後,陸青頭一回與人談及此事,心裡隱隱有些不自在,隻微微頷首,並未言語。
“去年那燭煙計失敗後,王浪蕩說要去請你相助,我還說決計請不動你,誰知竟被你做成瞭——唉!那毒煙蠟燭還是我熔制的,非但沒能動到老賊分毫,反倒害瞭棋奴性命⋯⋯”
王浪蕩是王倫綽號。溫德言罷,又重重嘆瞭口氣,眼中竟閃出淚來,他忙用手背擦去。
陸青淡淡應瞭句:“李彥替瞭楊戩。”
“我也聽聞瞭。”溫德又露出些笑,嘆瞭口氣,“此事便如我行醫,常會遇見些老病根,年年治,年年犯。可這些人上門來,怎好不治?治一回,多少能好一陣,人也能多活些時日。行醫,不過是跟上天爭時日。實在爭不得瞭,也就罷瞭。”
陸青頓時想起瞭因禪師那句遺言,“豈因秋風吹復落,便任枯葉滿階庭?”兩者言雖殊,義卻同。溫德面慈心善,天性和樸,卻又毫不愚懦,於善惡之際,始終能見得分明。
陸青自幼修習相學,見過無數殘狠卑劣,於人之天性,早已灰心。此時卻不由得贊同孟子所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乃萬物之靈,這一點靈光中,不僅有智,更有善。隻是,靈之為靈,極珍也極弱,如同冰原一點微火,略經一陣寒風,便即熄滅。能保住這點微光者,極少,卻並非沒有。佛傢有“薪火相傳”之說。這荒寒人世,正是憑借這些四處散落之微光,方能見亮,才得存續。而心中懷亮之人,如同暗室之中,對燈而坐,也自然比旁人安適淡靜⋯⋯
他正在出神,溫德笑著問道:“忘川之畔人何在?”
陸青也笑瞭笑,但旋即正色:“我是來尋王倫。”
“哦?你也未見他?去年十一月初,我跟他聚過一回,之後便再沒見他影兒。”
“我也是那時見瞭他一面。他被楊戩捉捕瞭?”
“嗯。不過,我也隻是聽聞。”
“方亢兄說王倫投靠瞭楊戩。”
“你莫聽他亂說,他隻是妄測。你我都該知曉,王倫人雖浪蕩,但絕做不出那等卑濫之事。”
“清明那天,他在東城外。”
“哦?我也正要說這事。那天,我趕早去東郊上墳,強邀瞭方亢一起去踏踏青、散散悶。晌午回來後,在汴河北街葉傢食店吃瞭碗面。才吃罷,便一眼瞅見王倫從店前急匆匆往東頭走過去,穿瞭件紫錦衫,以前從沒見他穿過。方亢背對著街,並沒瞧見。我怕他和王倫又爭罵起來,便忙付瞭錢,借口有事,讓方亢先走。等他走遠,我才急忙去尋王倫,一直尋到郊外那片林子,都沒尋見。後來才知,你竟也在那裡,楊戩也死在虹橋上。”
“王倫上瞭一隻客船。”
“他離開汴京瞭?”
“沒有。不過從此消失不見。”
“消失不見?”
“那船,是楊戩安排的。”
“這王浪蕩到底在做什麼?對瞭!我醫過一個海貨商人,他正月底去瞭登州,說在登州見到瞭王倫,身邊還跟瞭兩個漢子,神色瞧著有些不善。”
“正月十五,王倫托人給我捎來封信,那人說王倫在山東兗州。”
“兗州、登州,他一路往東,去做什麼?”
“不知。”
“我還聽個人說,前一陣在金明池邊,瞧見他和那個唱奴李師師同上瞭一隻遊船。這王浪蕩,浪蕩得沒邊瞭。我想去打問打問,可那唱奴的門,又不是咱這等人輕易能登——”
陸青聽瞭,心頭一寒:此前,王倫一心刺殺楊戩。如今楊戩已死,他卻行蹤難測,莫非又在謀劃新計?李師師曾得官傢臨幸,王倫接近李師師,難道想⋯⋯